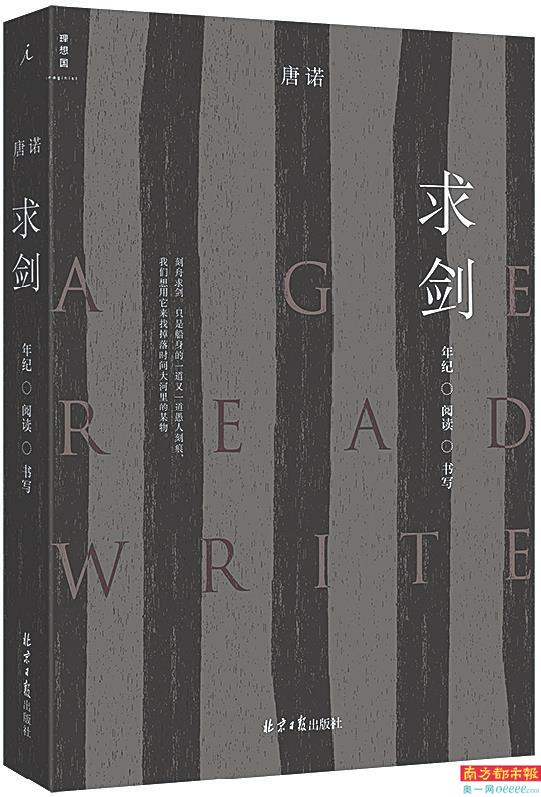
从《尽头》(2013)《声誉》(2018)到《求剑》,唐诺先生的书写节奏是如此稳健,而书写的内容则逐步扩张,向更深远、更宏大,同时也更关键的那些主题迈进。相较而言,《声誉》所处理的那些主题——声誉、财富和权势——是更重要而尖锐的,《求剑》所处理的主题——年纪、阅读和书写——则更像是唐诺自己的“主场”,范围虽小,但写起来更游刃有余,更能直击要害。
唐诺这一次拈出“年纪”二字,很能体现他对时代脉搏的敏感度。尽管他主要是从文学出发来触及这一话题,但有关“年纪”的探讨和认知实际上是可以迁移、扩展到其他很多领域的,换言之,“年纪”二字其实切中了整个时代之弊。
哪怕不怎么熟悉和关心文学的读者也都知道,有许多文学家,尤其是诗人,是短命的。济慈死的时候是25岁,雪莱则不满30岁,拜伦是36岁,普希金不满37岁即死于角斗,兰波是37岁,且他很早之前就不写了。小说家的命好像相对长一些,但天才拉迪盖20岁就死了,爱伦坡、卡夫卡、契诃夫都只有四十来岁的寿命,雷蒙德·卡佛活到了50岁。说这些干嘛?唐诺其实是想指出,许多文学家早早就死了这一事实,对于文学来说,是有意味的,甚至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提出,人生各个阶段的经历及其记忆的总体构成了一座“年纪的金字塔”,越年轻,离出生的时间点越近,金字塔的底部就越宽,越年老,越接近死亡,则金字塔细瘦稀薄,形成尖端。许多文学家在青年、中年时期就去世了,这就决定了他们相应地不可能有对中年、老年的切身体察;虽然说起来残酷,但他们的人生经验事实上是受限的,如果他们在作品中曾对中年、老年加以书写,那他们这些书写的品质其实是可以再推敲的。文学家的短命在文学中沉淀出的一个结果就是,如唐诺所言,“小说里散文里写的老人,一直是最样板化、最想当然耳的人物,甚至,假人。”(《求剑》第121页)
随着人均寿命的提升,当代作家们似乎有了一种天然的优势,即他们可以好好地写中年、老年的经验了,而古人则往往不能。莎士比亚在中国有一个习称、略称、尊称,叫“莎翁”。恐怕很少有读者会意识到,莎士比亚去世时是52岁,而唐诺写作《求剑》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他无论如何不应该管莎士比亚叫“翁”。当然,这绝不是一个辈分问题。莎士比亚写《李尔王》时才四十一二岁,他不可能在刻画垂暮的国王时利用上自己的亲身经验,我们自然不会说莎士比亚笔下的老人形象是“想当然耳”,但他的好会不会是有限度的呢?唐诺以他不凡的敏感意识到这个问题。
由于习惯从年轻而非从年长的视角考察文学,我们的读者在面对那些更成熟而非更富生命激情的作品时往往不能做出合宜的审美判断。唐诺在《求剑》中特别以张爱玲的《小团圆》为例指出,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实际上比她那些广为人知的早期作品要成熟得多,而大部分读者熟读的张爱玲作品都只是她30岁之前写就的——对此,我甚表赞同,尽管《小团圆》的后半部写作并不完美,但它的前半部的确是精纯无匹。
在当代世俗社会,有一种对停留在青春状态的痴迷,这种普遍的心理与文学世界中积淀的结果相叠加,使得我们常常不能也不愿去品鉴那些更成熟的作品。如唐诺所言,“大众化,其永远不易的色彩便是年轻。”(第126页)而他更直指失却了判断力和责任感的文学评论界:“近几年来一个更醒目的现象(或趋向,方兴未艾),则是严肃的文学评论评价向着一般阅读现象的持续靠拢,有那种敌众我寡的弃明投暗味道,不是人走向山,而是山乖乖走向人;不是一般阅读提升,而是文学评论慈眉善目配合,特别是文学评论交由学院、由大学文学科系全面接管之后,因为这是一个缺欠生命经验稠密度的地方,也是一个隔离的、时间感倾向于循环重复而非前行的地方,遂也是一个最容易也最快速年轻化的地方,正由殿堂一一改装为夏令营。”(第122页)
尽管年纪并不必然就是成熟的刻度,但有了一定年纪的写作者的生命质地无疑是更坚实的。因此,唐诺提出,我们应更重识中年,“尤其是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因为“人类所做成的事,几乎集中在中年这段人生场域发生”(第30-31页)。他还慨乎言之:“我尤其喜欢那种没生物性命令在其中、人纯净的自由,是一种更自由的自由。”(第30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转而关注唐诺在《求剑》后半部所处理的一个主题:创作者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而它实则也与自由相关。在“文学书写作为一个职业,以及那种东边拿一点西边拿一点的脱困生活方式”这写得非常精彩而又深刻的一节里,唐诺谈及创作者保有一个自由身的重要性。但在这一问题上,普通的当代人未必能理解书写者为何对自由有那么多的需求,因为“现实里我们一直看到的正是:大历史走向里,人们一开始热烈欢迎热情拥护自由,但逐渐收束转向要稳定和安全;个人的生命时光里,人年轻时日向往无羁,随着年纪随着身体的种种变化,地心引力拉下来也似的,寻求的是安适和平静”(第296页)。唐诺不无沉痛地指出,“这趟自由的历史折返之路,正是人们不断发现自己真的不需要这么多自由”(第298页)。而创作者则不然,他们宁愿放弃掉一些东西,而换取“不可能平滑如镜没瑕疵”(第295页)的自由。
在中文世界,唐诺以其独有的、充满韧劲的写作,开拓了书写的自由之境,引领读者不断思考那些幽暗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事物。他的言说,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倾听的声音之一。 (乔纳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