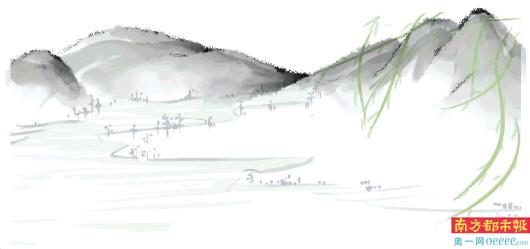
□文/丘玲美(梅州)
编者按:南都语闻“回乡笔记”征文自年前启动以来,已收到投稿千余篇。我们将精选部分优秀作品,陆续刊发在南都语闻周刊上,以飨读者。下面这篇,从家乡一湾河写起,写出了河边村庄和人的变化,写出了自己的乡愁。
元旦假期回家,依旧习惯性地绕到屋后河边走走看看,尽管那河已不再是河。
河没有名字,就让我冒昧地用自己的村庄给它命名,姑且唤它白河吧。
1998年以前,白河宽超过五米,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水草随波荡漾,鱼虾嬉戏其中,石螺蚬子藏身于卵石间,偶尔悄悄探出头。白河的两岸,是一垅垅密集的菜地,以及结满小果子的苦楝树。
夏天的早晨或傍晚,母亲携我到河边菜地劳作。这六分地,是从奶奶手里传过来的。菜地土壤肥沃,毗邻白河,浇灌方便,菜地的边上,还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奶奶执意要把这块最好的地留给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听母亲说,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分家时,为了这块地,二伯母还在奶奶的厨房门口骂了几天。
母亲从白河里把水一担担挑上来,我则除草松土。白河里温柔裹着三五成群赤条条泅水打闹的孩童,偶有石头扔进河里溅起来的水声和嬉笑声传来。河边三三两两排着浣衣洗菜的主妇,东家长和西家短,在棒槌与衣服敲打声里,被掰开、被碾碎。偶有高挽着裤腿、手握尖竹的男人站立河中,一次次把竹竿向白河里自在游荡的鱼身上扎去,又一次次故意被卵石打滑。婆娘们见了,笑骂一句“屙痢屙肚”(客家俗语,很差劲的意思)。有时嬉笑声摇荡下一颗苦楝子,砸在浮水孩童的头上、身上,或屁股上,于是嬉笑更甚。
我的老家在离白河约一公里的村里,是一栋两层带天井的水泥房,与几位宗亲的土坯房连在一起。父亲初一辍学后,便辗转武平、平远、梅县等地,倒腾腐竹、橙子之类的土特产回来卖,也去白河摸螺捞蚬,去山上石洞里掏蛇捉蟾蜍,勉强能养活自己。后来父亲娶了母亲,从奶奶那儿分得几只碗、几双筷子,还有一间灰暗的房间作新房。除此之外,最值钱的,便是白河边上那六分地了。
再后来,父亲进了当时在家乡赫赫有名的水泥厂,做了一名伙房厨师,每个月才有了固定收入。母亲则在那六分菜地辛勤劳作,产出的菜蔬和自己泡发的黄豆芽绿豆芽,全部供应给父亲所在的伙房。便是靠着这六分菜地,父母亲才攒下了这笔建房子的钱。
那栋二层的水泥房,我的老家,从我记事起便傲然矗立在一列列土墙青瓦砌成的四合院中间。在我识得几个字后,还煞有介事地把它叫成“天渊阁”。
上世纪90年代我的“天渊阁”,有“四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音响),却独独没有卫生间,如厕要到门口的公共茅厕。那时候上厕所,除了要忍脏臭,更要忍怕——怕一不留神便踏空,掉进粪坑里去;还怕在墙上、踏板上爬来爬去的蛆虫,让人汗毛直竖。尤其是夜里,除非实在忍不住才去茅厕,去也要喊上弟弟或堂姐妹陪同打手电。弟弟顽皮,经常熄了手电发出怪叫,吓得我两股战战,只能速战速决。每次如完厕,身上味道袭人,不站在风口吹几小时不能散去。
离“天渊阁”不远处还住了位腿脚不便的孤寡伯姆,母亲说,算起来跟我们家还有点沾亲带故。每日清晨,伯姆便手捏两条稻杆,深一脚浅一脚地远远踱过来,踱过我家门口,再踱向茅厕。那捏着稻杆的手势,那怪异的走路动作,弟弟学得惟妙惟肖。而我们那时只懂得笑。
还有一次捉迷藏,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提出藏在茅厕。于是我们五六个小伙伴掩住口鼻,一边忍笑一边又示意别人噤声,挤挤挨挨的,竟把二堂弟挤进了茅坑。婶婶惊慌失措,拿来抄网才把二堂弟捞了起来……关于农村茅厕的记忆是“痛并快乐”着的,农村人垦殖荒地离不开厕肥,它与村庄、与家连在一起,早已变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父亲在伙房时,眼见着潲水每日被别人挑去,“肥水流入外人田”。与母亲商议后,连夜在老家旁边建起一个猪圈——养猪。猪圈最高峰时期,等着出栏的肉猪就有二十多头。就这样,凭着踏实勤劳和活泛的头脑,父亲又攒下了在白河边建新房的钱。
于是那六分地被囤平了。地基夯实了,框架浇筑好了,墙刷了,地板瓷砖贴好了……千禧年,全家如愿搬进了新房。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推开窗就能看见白河流淌而过。夏夜,河风拂动纱帘,伴随着水流声、蛐蛐声入眠,梦也是甜的。
家乡丰富的石灰石蓄量,带动了水泥产业的繁荣发展,也兴盛了村镇经济。205国道穿镇而过,疾驰的车辆,把河砂、砾石、石灰石和成品水泥从这山沟沟里不停歇地运输出去。小时候经常仰望的那座山,一年一年地瘦下去、矮下去。空气里弥漫着水泥灰,家里的窗户常年紧闭。冬天刮北风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出门,因为一出门,便是“尘满面,鬓如霜”。
白河边的菜地渐渐被鳞次栉比的房屋替代。这是一个家家户户都有了洗手间的年代,这也是一个庄稼人已鲜少种植,不再垦殖荒地的闲适年代。在搬来新家前,老家被父亲以极低的价格转售给了一位宗亲。我已鲜少回去“天渊阁”。
有次和母亲谈起拿稻杆的伯姆,母亲说,人早已不在。末了又补一句,老家门口的那几座茅厕,全塌了。
慢慢的,白河变窄了。两岸的房屋簇拥着它,把它越挤越窄,以至于今天我看到的,竟只是一湾浅浅的水沟。再没有主妇到河里浣衣洗菜,也再没有孩童钻入河里泅水打闹。在不刮风的傍晚,车轱辘停了下来,漫天的尘土也停了下来,我曾一次次沿着国道漫步,举目四望,却寻不见一棵苦楝树。
白河水时清时浊,浊时多过清时。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品尝过它的甘甜洁净,乡村的土地也品尝过,白河哺育了一代人;在我长大成人一次次想逃离家乡的时候,白河还是默默地,用它已经干瘪的身躯承担起采石场、水泥厂和两岸居民的排污责任。它伴随着我的成长流淌了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忍用“苟延残喘”形容它。
我曾经从生身之地的源头出发,走了一程,又甘于重返和扎根原乡。身体安顿了,灵魂却总是在飘荡。我也不知道乡愁的愁从何来——它浅浅的,又总是夹着一丝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