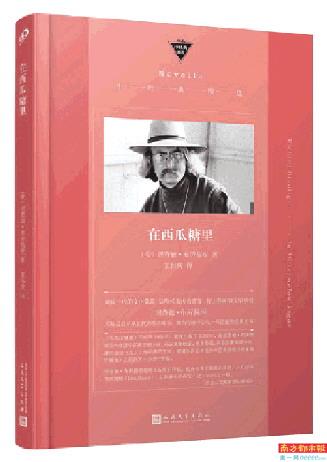
《在西瓜糖里》,(美)理查德·布劳提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55.00元。
□ 赵瑜
读完《在西瓜糖里》,我对作者布劳提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果然,细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即刻懂了他的那些怪异的用词习惯源自哪里。原来,他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啊。高中毕业后,他因为向警察局的窗子扔石块而被捕,后来被医生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和抑郁症。
不得不说,《在西瓜糖里》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小说文本。作者极尽了想象力。比如,在小说里,他虚构了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没有固定的名字。也就是说,他虚构了一个可能是所有人的人。
这就很有趣了,小说里的人物竟然没有名字。至少,布劳提根挑战了小说对人物固有形象的描述。是的,全篇小说里,没有对“我”的样貌的概述。
阅读《在西瓜糖里》的感受有些像读安吉拉·卡特,而布劳提根的这部小说便有些像暗黑的童话一样。比如,他设计了两个地点,一个地名竟然叫“我的死”,这真是荒诞,哪有叫这样地名的小说。这可能是我阅读的一个边界,我第一次在小说中看到一个如此不正经的地名:我的死。小说中另外一个地点竟然是遗忘工厂。如果说,我的死这个地点里发生的故事象征着现实世界,那么,遗忘工厂里的事,更像是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残酷无比。
这样来理解布劳提根的写作,便有了一个进入文本的钥匙。布劳提根的想象力略大于普通的写作者,除了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以外,他在他的小说文本里进行了各种发明。比如,他让太阳每天的颜色不同,以对应星期一到星期日。星期一的太阳是红色的,星期二是的太阳是金色的,星期三比较厉害,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灰色的,而且不出声音的,星期五是白色,星期六是蓝色的,星期日呢,是棕色的。
布劳提根喜欢星期四,因为太阳是灰色的,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灰色的。又因为这一天是不出声音的,所以,这一天不论制造什么东西出来,都是没有声音的,哪怕你做一个闹钟出来,也是不出声。这样对小说进行设计,过于孩子气。然而,却又让读者觉得风趣。小说里的老虎和人一样,会说话。但是,老虎将小说中的“我”的父母吃了。一边吃“我”的父母,老虎还一边向还是小孩的“我”道歉。老虎仿佛也是一种比喻,它们既有可能是现实中某一种权力,比如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也有可能是族群的歧视,比如二战中,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
而小说中对遗忘工厂的描述,则更像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国家共同的隐私。哪个大国不都拥有一个全民族的共同的“遗忘工厂”?这样的例子可能有着泛世界性的,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常常遇到的现象,而在小说里,布劳提根只是让一群酒疯子“阴死鬼”和他的朋友们住在那里。
而这个遗忘工厂里有什么呢,布劳提根是这样描述的:“有时,他们会把一个喝醉的同伙弄醒,派他进城去卖被遗忘的东西:那是些特别好看或奇怪的东西,或是几本我们当时拿来烧火的书。遗忘工厂里这种东西到处都是,有成千上万件。他们用被遗忘的东西换回面包、食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除了挖掘和喝酒,他们用不着干什么。”
这一段话里简短介绍了遗忘工厂里的东西,接下来,布劳提根还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句式来介绍遗忘工厂的布局或者是幅原是多么大。他这样写道:“遗忘工厂就这样往前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延伸。你明白了吧。它是个大地方,比我们大多了。”
不止是在内文中,如此任性的重复使用词语,来增加表述的程度。布劳提根在小说的标题制作上也有这样的抒情方式,比如第二部《阴死鬼》中有一个小章节的标题竟然是《又是又是又是又是玛格丽特》,是的,四个又是。读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要疯掉了。
似乎,表面上,《在西瓜糖里》是一部爱情小说,我抛弃了玛格丽特,喜欢上了一个叫保琳的姑娘。然后,玛格丽特心碎,痛苦,失落,妒嫉,难过,最后上吊自杀了。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表面的叙述结构。而在这表面的故事背后,又藏着一个开放式的想象力博物馆,“我的死”这个地名,究竟与一九六十年代的美国有什么互文的关系,而遗忘工厂,究竟是想要暗喻哪一种文化结构的国家。
老虎呢,那两只吃掉了“我”的父母亲的老虎,最后被人类给杀掉了。老虎代表着什么文化,是土著居民吗?
这部《在西瓜糖里》与其说是一部梦境式的小说,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摄影作品集的解说词,全篇小说充满了空白感,多义,指向不明,以及色彩斑斓的想象力。
我特别想摘录一段关于想象力的描述,是小说中的棚屋,布劳提根这样写道:“保琳的棚屋全部是用西瓜糖做的,除了门是一棵美丽的、带灰色小点的松树,上面有一个石头把手。就连窗户也是用西瓜糖做的。这儿的许多窗户都是用西瓜糖做的。经过做窗户的卡尔一加工,糖和玻璃就很难分辨了。这种东西完全取决于谁来做。这是一门复杂的手艺,卡尔会这门手艺。”
读这样的文字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总觉得他的描述中布满了陷阱,可能表面上他说的是门,是窗,而在本质上,他是不是在说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呢?
布劳提根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29岁,正是一生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间。然而二十年后,刚满五十岁的布劳提根自杀身亡。对比这部小说中,“我”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了玛格丽特的自杀过程。他仿佛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