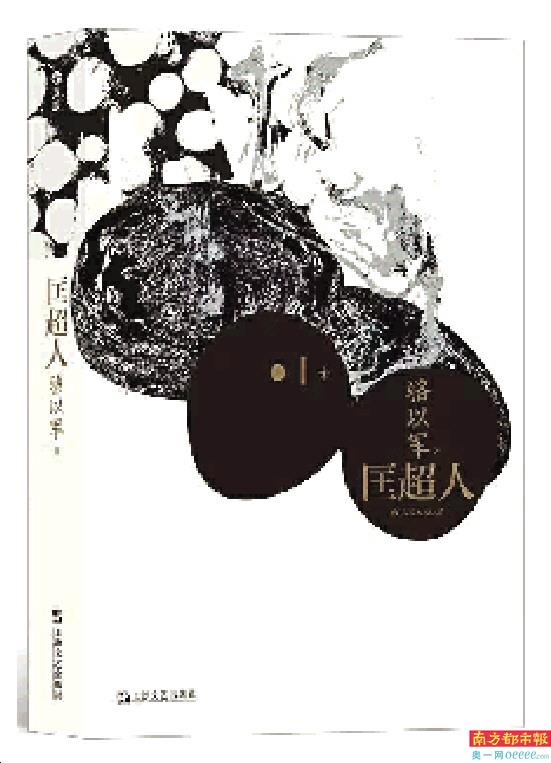
骆以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多年来,小说家骆以军一直以无畏的精神、秾丽的文体冲击着“小说”这一文类的边界,《匡超人》是他的又一轮猛攻。作者的想象力上天入地,尽情驰骛,另一方面,他对世俗社会的观察和洞见细入毫芒。在这部小说中,脑洞与破事齐飞,尴尬共悲哀一色。在中文世界“伪/准现实主义”弥目皆是的当下,它显得如此孤高、如此触目。
《匡超人》是一部实验性的小说:它有情节,但它的情节不像传统虚构叙事那样遵循“起承转合”的模式,简单地说,它没有讲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它的情节是片段式。许多个的片段,由主人公的思绪串联,繁密地拼贴起来,组成一块色彩斑斓的织体。不过,《匡超人》又完全不像我们以往读到的“实验小说”那么晦涩、对读者的智力和耐心发起那么大的挑战,它也不用“实验小说”那些叙事的奇技淫巧。《匡超人》是非常好看的,读来畅快淋漓。它是一部极别致的实验小说。
既然没有完整的故事,要概括小说的情节就变得相当困难。如果不嫌过度简化的话,我们可以说,《匡超人》主要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美猴王,他跨越时空,经历已然颓败、残破的文明洗礼,来到当前,尽管依旧落拓不羁,但早没有了当年横扫六合的气势,是沉沦于俗世的孤独神祇。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作家骆以军的一个分身,一个同时承受着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的文人,面对熵值无止境增长的现代文明,在对往昔的恋栈与对刻下的沉迷间踯躅,不知前路在何方。在后面这条线索上,还有“大小姐”“老派”等角色,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际遇为小说添上一抹猎奇的情调,然而,这些奇特际遇无一例外地为黯然怀旧的色彩所浸染,如同“白头宫女”的夸说。上述两条线索相互缠绕杂糅,随着叙述者思绪的跳荡激射,任意蜿蜒。
骆以军独具特色的华丽文风,在《匡超人》中变本加厉。也只用引用,才能让没读过他作品的人明白,那种“华丽”指的是什么。我们且引涉及《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唐僧冤枉的一段,看看骆以军的文字究竟有何特点:
这一段情节,或是写到了中国古往今来所有读书人的痛点哭点酸楚的敏感带。因这个文明,正是“冤屈”“忠义之人被屈杀”的生产装配线啊。而这个文明,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的SM痴迷、尊崇;恰恰又总像乔木必被藤蔓缠绕,搭配着那臻于化境的,颠倒黑白之术,落井下石之术,谗言毁谤的人言可畏,谄媚弄权的精密技艺……这一切相生相克。集体潜意识里,看到此章莫不咬牙切齿,为悟空叫屈。骂翻三藏之迂蠢,与猪八戒的小人嘴脸。这样的冤案,这个心灵史的长河,记下了无数像悟空那么冤屈,但却无悟空的法术本领,也无花果山可回的不幸忠良。如屈原、伍子胥、司马迁、于谦、岳飞、史可法、张学良……太多了,像数夜空之繁星,一片紊乱纷繁。而孙悟空这出戏替他们泄了那郁愤冤苦。整本《西游记》,其实就是一整座关于幻术的大游乐园:你用幻术诈我,下一回我用幻术婊你。就连被打死的,都带有一整孩童的纯真和嬉闹。这是这个民族长久在权力隧道车的黑暗轨道上,让自己变成不那么被恐怖景观吓哭的孩童。一切的粗暴、恐怖、冤狱、市曹分尸、砍头、吊刑,最后都像孩童的嬉要一样,带着纯阳童子气。像美猴王。(第119页)
整部《匡超人》就在这样泥沙俱下、呼啸席卷的议论中向前推进。这些议论奇特、透辟,其中蕴含着对历史、家国、文化的反思、体察和调侃。美猴王和骆以军分身之间的对话,则像是骆以军的一个分身与另一个分身在左右互搏、争辩说服。
正如王德威在书前导读文字中所云,《匡超人》“既悲欣交集又插科打诨”,它把一种五味杂陈的现代人“失路”之感表达得淋漓又痛切。从形式上说,它摆脱了现代小说叙事首尾完具的束缚,依循独特的路径,展开自己的铺张扬厉。这一形式,让我们忆起汉代辞赋的汪洋恣肆、藻饰斑斓。事实上,《匡超人》就像屈原、宋玉的辞赋一样,以辞藻声色抒发失意怅惘,只不过,这失意着眼的,不再是个人遭际的沉浮,而这怅惘针对的,早已是人类文明的升降了。 ◎ 黄景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