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华栋 小说家,诗人。祖籍河南,生于新疆,16岁开始发表小说,18岁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任研究员。曾任《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等。出版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800多万字,单行本近百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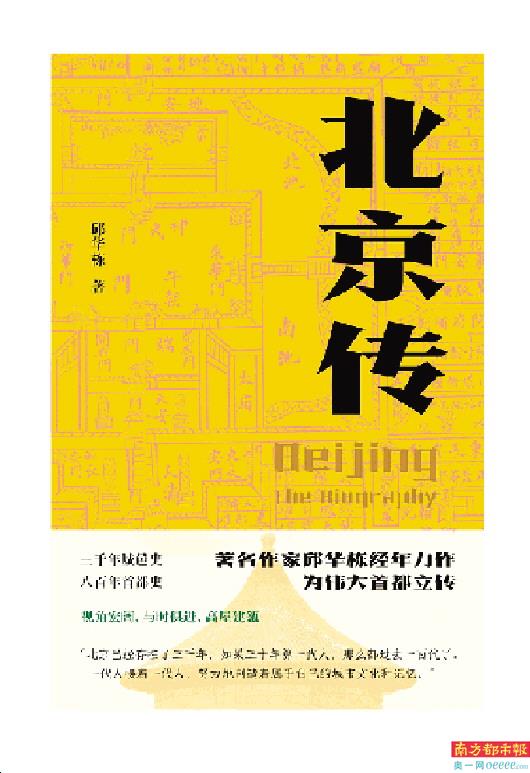
邱华栋本来设计了两个版本的《北京传》。繁版80万字,副题野心勃勃——《时空中的人与万物》。简版20万字,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切入,对浩瀚史料万取一收,凝练利落地叙述北京3000年的城市史。
被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部的太行山脉所环绕,在北京湾这块扇形平原上,先后诞生了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和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特别市,以及今天的新中国首都北京。
在《北京传》中,邱华栋以时间为线索,细述北京城的前世今生。“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三千年,城市像地衣一样,紧紧附着在大地上生长。风云变幻,王朝更迭,旧城的废墟上不断“长出”新城。新城又在时间之茧中再度磨砺、蜕变。
邱华栋是“新北京人”。他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迄今已有28年。刚来的时候,他一度住在长城脚下的村子里,每天蹲在一段野长城上,感受这个城市郊野的粗犷气息。巨大的好奇心促使他不厌其烦地研究北京城的方方面面,小到郊区的一朵野花,一片草叶,大到海浪般静寂起伏的天际线和隐秘错杂的下水道系统。二十多年间,他搜集了四五百本有关北京城的书籍和史料,与此同时,他又作为城市生活的参与者与建构者,穿行于四通八达的街巷,见证后工业时代这座国际大都市令人讶异的快速发展。
2016年,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关于伦敦城的“锦绣之作”,几乎立刻激发了邱华栋写《北京传》的雄心。在繁版80万字的设想里,他和阿克罗伊德一样,意图建造一座城市的迷宫,时间、人与万物在其中纵横驰骋。而最终实现的简版,更像一个清晰的指引和劲健的骨架,它是邱华栋与繁忙的日常工作妥协的产物,是对庞杂的材料刀劈斧斫的结果。它的主章与副章的层叠结构,仍暗藏着被持续书写、无限丰富的可能。
作家张新颖在读了《北京传》后说:“华栋本来是一个很有表演性的人,他很愿意显示自己才华的各个方面。但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像变了一样,他很谦卑,很耐心,很细致。”
而在邱华栋看来,人并非城市的主宰,人附着在城市的空间当中。北京有3000年的城邑史,在这座城市中生活过一百代人。他在《北京传》的后记里写道:“我们这些城市的过客和大地上的短暂栖居者,必须谦逊地对待城市。”
作为一代新北京人,他倾慕当代的北京:摩天楼立面流动泛光,环线如层层漾开的钢铁涟漪,整个城市敏捷、年轻、开阔、舒展。他在许多地点观察过北京的城市天际线,以景山山顶的观景亭看出来最为动人:
“城内都是青灰色的胡同四合院,一眼看上去平缓美丽,视线里没有多少高楼和大烟囱,全是灰瓦的胡同民居。天气好的话,西部和北部的一抹远山,山体的黛色衬着天空之蓝,绝对是一个好视角。那个时候,北京360度扩展的城市景观,波澜壮阔而又波澜不惊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着眼于北京城空间结构的变化
南都:请谈谈写作《北京传》的缘起。
邱华栋:2017年,读到《伦敦传》,挺兴奋的。英国作家阿克罗伊德把伦敦当作一个人来写,这种意识打动了我。我特别喜欢那本书,受了很多启发。实际上我积累了20多年关于北京的资料。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以后,就有意识地开始收藏,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起码有四五百种。看了《伦敦传》以后,激活我想写一本《北京传》。
2017年有一次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他问我干吗呢,我说我在读《伦敦传》,然后说我也能写一个《北京传》,有点儿开玩笑的性质。结果那么一说,过了一星期他就把合同给我寄来了,还预付了一点稿费,是他们出版社申请的扶持基金。这样我就“上套”了,不写还不行了。
因为工作太忙,我一直在看资料,一直在想怎么写这个稿子。真正下笔的时候,我发现对象过于庞大,不太好写。
原先我列了一个大纲,副题叫做《时空中的人与万物》。我原来想写80万字,试着写了两章。一章叫《90年代的一个夜晚》,写了一个人穿行在夜晚的北京,从傍晚6点一直到凌晨2点,写了2万字。写完以后发现太个人化,比较文学性,所以那一章我放下了,也没有收入成书的《北京传》里,其实它充满了个人的有意思的观察和经验。
我继续寻找新的写作方式。后来想了想,一口气拿出一个80万字的书,从我个人的精力来讲,从出版的节奏来讲,都很麻烦。所以我决定写一个简版,干脆利落的,把北京3000年城市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写出来得了。确定了由繁版从简版的转变,是我这几年时间里内心的一个变化。
这样我自己心里松了口气,一下觉得比较有把握了。我有一个对象的设置。原来我设置的读者是我的文学同行,他们看了我这80万字以后确实很惊叹。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设定为,一个普通人来到北京,他买了这么一本书一看,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伟大首都北京的3000年历史是怎么回事儿。我把目标调整了,实际上扩大了受众,把个人化的感觉、经验、视野隐藏起来,变得比较谦卑。
南都:《伦敦传》浩瀚驳杂,而《北京传》具有一个以历史为线索的相对清晰的体例。能谈谈《北京传》在取材上的考虑吗?
邱华栋:我不想写成一个“历史上的人和事儿”,不想去重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个城市它像一块地衣在大地上生长,我主要着眼于随着时间推移它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比如最早它是蓟国的首都蓟城。到燕国的时候,它作为燕国的都城,它在什么位置,它有多大规模。到了汉代,它是广阳郡的郡治,相当于一个省和州府之间的行政区划。比地级城市大,比省会城市小。到了唐代它又是幽州。
特别是当代,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城市主政者总体的规划,京津冀怎么一体化,新机场落成……主要是突出空间感。在这个空间感里有一个时间的线索。基本上是薄古厚今,越往后笔触越细腻。当然涉及到1949年以后很复杂,各种历史事件对北京旧城改动得比较大,也比较有争议。改革开放40年以来北京城的变化也非常大。我原来80万字的计划里其中有40万字都是当代的。
我看了两本《南京传》,包括叶兆言老师的和张新奇先生的,一个写到民国,一个写到1949年就不往后写了。我认为,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首都,它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突出了。现在,北京变成了世界十大都市之一,所以我的视角、感受,和其他几个作家不一样。
我个人性格是喜欢《伦敦传》那样磅礴的、芜杂的东西,它适合我这么一个新疆长大的北方人。但实在是工作太忙了,20多万字的简单版我觉得也实现了我的构想。我以一个小说家的剪裁得当,行文简洁明确,一章章刻画具体,加深了读者对从古到今,特别是今天,2020年的此刻的北京城市空间的理解。
南都:请谈谈《北京传》全书的结构即主章与副章的构想。采取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什么?
邱华栋:主章我主要是写的城市的主体结构的变化,比如说从唐代的幽州城,到辽代和金代的五京之一,到元大都,城市的位置、空间就不断地在移动,在改变。我在主章里主要叙述这个变化。
副章,选两个小点儿,来突出这个年代北京城的特点。比如金代最突出的是燕京八景,这个说法是金章宗提出的。到了清末民国,东交民巷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涉及到跟西方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比如说老舍是写北京的本土大作家,我就把他拎出来单列一章。骨架是主章,副章我考虑以后可以无限增加。比如我手里还有很多材料都没放进去,比如北京的野花有哪些,北京的动物,北京的植物,北京的下水道系统……无穷无尽,可以一直往下写。
主章写到不同年代、朝代的城市空间感,副章就带有我个人的观察。比如写到潭柘寺,那是我自己去的,仔仔细细地在寺里来来回回地跑,待上一天去观察,我自己的体验会强一点。
北京家长、大妞和国际化的帅哥
南都:这部书写了多久?写的时候状态如何?
邱华栋:事实上这个书我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春节前后有疫情,在家里,哪儿也出不去,一天一万字,一个月就写完了。但看材料的功夫是用了20多年。然后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就给出版社了,并没有费什么劲儿。
写的时候,每天写一章。我的房间里挂满了地图,大概要摊开那么二三十本书,然后思考材料怎么使用,如果能找到那个时候的音乐也拿来放一放,比如古琴、古筝、民乐,什么都有。有关的图片,比如辽代契丹人的衣着,有些画册也得打开看。总之是要唤醒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每天书房里头都得换布景。把各种地图、各种材料,变成当下要写的这一章的内容。越往后越现代,到了当代就得放各种高楼的图片,我的《世界建筑》杂志,大量的北京所有高楼的图片、画报,书房里摆一屋子。就这么一口气写下来。
南都:城市传记有别于地方志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在读者的期待里,它应该是活的,具有生命色彩的,具有写作者的个人特色的。在《北京传》的写作中,你如何在“述史”的同时突出个人的声调?
邱华栋:个人色彩主要在于我对空间感的一些体会。刘心武老师也对建筑很关心。他说过,建筑我们不要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城市我们也不能从街道上匆匆而过。我们要进入建筑的空间,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去感受这个空间,才对建筑有所体会。你还要使用建筑里面的东西,比如说洗手间、大堂、咖啡馆,是个酒店还得入住它的房间,你才能获得对这个空间完整的感受。
所以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在北京去的地方多,在一个大楼里上跑下跑,外面看看,里面走走,感受具体的空间感。比如,关于通州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我经常自己开着车来回转,体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空间感。有机会进到现在北京市府的大楼,我也找朋友呗,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建筑。比如北京大兴新机场,这几个月出差,我有意识选择在大兴机场出发降落,有几次我一个人在里面泡了一两天,感受它进出是否便捷,空间设计、装修材料、采光,种种方面把它和三号航站楼做比较。我对这些建筑观察得还算比较细,有很多个人的体会,跟书斋里的学者写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学者更多依赖于材料,而我呢,我觉得写一个城市,你一定要像城市里的一个活物,你得在城市里到处走动才行。进到建筑的里面,进到街巷里。具体感受就化作了个人化的表达。
南都:你如何看待“城”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指帝王将相,还有城市里三六九等的小人物。在一部城市传记中,城中的“人”应该占据什么地位?
邱华栋:我觉得人是附着在城市这个空间当中的。我不是太喜欢写王侯将相,虽然他们是城市的主要统治者,事实上,北京两千多万人,芸芸众生才是城市的主体。
目前这本书主要是着眼于空间的变化,把王侯将相也放到次要的地位来审视,如果说再写一个80万字,更多的可能都是城市日常生活的情况。因为日常生活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是当记者出身的,好奇心特别强。我也观察过一个煎饼摊一个上午的运营。我去看那卖煎饼的一天卖多少张煎饼,每个时段多少张。北京捡垃圾的人是什么网络结构,我也做过调查。我原来认识一个从湖南来的捡垃圾的老头,认识了二十多年,他们有他们的网络,他们县有好几万人在北京收废品,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废品的,从哪儿收,又到哪个中心点处理,他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有他们生活的空间。
包括胡同里的生活。涉及老北京胡同生活有很多材料,我都看过了,但我想了想,我都没有往里写,我想以后再说吧。
南都:在《北京传》的结尾,你描述了一个高度数字化、充满未来感的未来城市。如果这种愿景成为现实,北京如何与其他国际化都市如巴黎、伦敦、纽约相区别?
邱华栋:技术可能是通用的。比如说手机的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但人还是在塑造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由当地的气候、风物构成的,它一定是有识别度的。北京这个地方干燥,喜欢吃牛羊肉,人的性格也改不了,生活习惯也改不了。另外,北京作为首都,它的政治性也很突出。这些恰恰是这个城市不变的东西。它的地域文化,不管外在的建筑空间、通讯工具,智慧城市的信息方式如何改变,人本身还是地域性的人,还是携带着这个城市的特点。
南都:你觉得北京算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吗?
邱华栋:实际上,真正伟大的城市我觉得也就那么十来个。伟大的城市首先要有规模,只有十万人或八十万人我觉得还不够伟大,至少得一两千万人。同时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方面,一定是非常突出地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域,是一个特别醒目的人类聚落集中点。
现在恨不得每个城市都要写一个传记,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我刚才又把我的那些书理了一下。我大概有十几本关于城市史的书,都翻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出版。包括伦敦传、罗马传、巴黎,关于纽约的有好几本,还有伊斯坦布尔、柏林、威尼斯、彼得堡、东京,其实也就那么十来个。好像其他的小城市我也没太大兴趣。北京应该能跻身到伟大城市的行列。
南都:如果把北京比作一个人,你怎么概括他的性格?
邱华栋:北京不是太好概括。北京起码由三种人构成。一种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威严的一个大家长,一个老头。但是他内心很慈祥,容纳着家族的每一个人在这儿生活,对每个人都很关心。还有一种就是北京大妞,很不在乎,大大咧咧的,很豪爽,很朴实,很大气,还有一些女性的柔媚。同时,北京到了最近的一二十年变得更加国际化了,有它非常帅气、年轻现代的一面,像一个穿西装的帅哥。所以用一个人比喻北京是不行的,我觉得应该是三者的结合。
北京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包容性
南都:很多从外地来京的人对北京这座大都市都会有隔阂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融入皇城根儿下这座城市的氛围里的?它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邱华栋:我是个北方人,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违和感不是太强烈。特别是当你在这个城市里有了固定的居所以后,你的心态就会变化。比如你买了个房子,你就变成了城市的一个细胞,你的主体感就增强了。如果你是个京漂,整天居无定所,你会有漂泊感。所以固定的居所很重要。我大约1998年在报社的时候就自己贷款买了房子。买了房子,立马就成了新北京的栖居者,没有漂泊感了。
北京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它的包容性。虽然我们知道北京人有他的傲慢、冷漠的地方,但实际上又有巨大的包容性。它既然是首都,就是整个中国人的首都。它不会排斥从任何地方来的人,只要你有能力在这里待下去。最大的魅力还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第二,北京是一个文化首都。我自己是一个文化人,这个地方的信息量巨大,最优秀的文化人很多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也能接触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杰出文化,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中国,肯定要在北京停留,在其他地方你见不到。一些乐队演出,一定要在北京演一场,在上海演一场,在广州演一场。其他地方未必去。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读台湾作家的作品,看到白先勇他们去纽约听一场伦敦交响乐队的音乐会,很激动。现在我在北京也能听到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不用去纽约了。这是跟其他二线、三线城市最大的区别。
南都:你的许多小说也是以北京为地理坐标和精神坐标。对一个作家来说,在小说里写北京和为北京立传,这两种书写给你带来怎样不同的体验?
邱华栋:《北京传》是把北京作为一个庞大的主体去观察。它是一个已经存在了三千年的空间。小说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以自我的内心表达作为主体,它与把城市作为主体刚好反过来。所以小说写作纯粹是个人的事儿,是一个生命个体的经验以文学的方式固定下来。你去写一个城市,如果你把自己摆到里面,你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当然也可能互为镜像,如果这两种我都写得很好了,以后会形成一种参照。像老舍先生就做得极好。《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与此同时又是中华民国时期多么重要的一个底层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好的作家的境界,我肯定还没达到。
南都:张新颖说你在写《北京传》的时候,比较不那么像平常那样天马行空,或者说不那么张扬,而显得谦卑、耐心、细致,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这种转变是什么造成的?
邱华栋:实际上也是我有意为之。北京作为一个题材它太难hold得住了。比如叶兆言老师,叶家三代人都跟南京有关系,写南京只有叶兆言最合适。一说南京,非他莫属。但是写北京,并不是非我莫属。我只能算能写北京的人之一。因为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对这个城市好奇。我住了28年了,这种好奇心是有的。所以态度上来讲,我在后记里也说了,这个《北京传》是我自己的,你愿意写你写你的,千万别觉得我抢了谁的行当,尤其是那些老北京。他们心里不服,说,这家伙怎么写出一个我们的北京传呢?但我觉得,北京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一个心态,自然会变得比较谦卑,作为小说家的主体性自然会隐藏在时空的变化里,变得比较渺小。
当然我还是雄心勃勃,希望再过几年,等我退休了或者有时间了,我把那个80万字的《北京传》写出来。
南都:如果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你最愿意造访哪个历史时段的北京城?为什么?
邱华栋:唐代吧。因为唐代的幽州是一个边陲城市,就跟我长大的乌鲁木齐郊区是一样的。当时的幽州各种民族都有,诗人也跑到这儿来,陈子昂跑到这儿来,登到一个台子上赋诗一首。各种民族、各种风俗汇聚在这里,是一个边陲的军事城市。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在这儿激荡,有很多可能性,你会见到很多奇怪的人,有趣的人,能喝到很多好酒,还可以写诗,相对而言有很大的开放性,所以我觉得唐代的幽州应该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