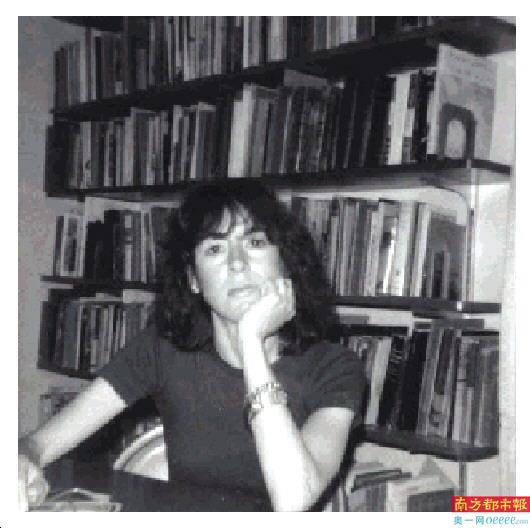
年轻时的诗人格丽克。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黄茜 10月8日,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获奖,理由是“她无可挑剔的诗意之声,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存在有了普遍性”。随后南都采访了几位译者、诗人,请他们谈谈格丽克其人其诗。
她写出女性的独特体验
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她在随笔《诗人之教育》一文中讲到家庭情况及早年经历,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拒绝上学,想当作家。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想,投身商业。格丽克的母亲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对两个女儿悉心教育,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以鼓励,及时赞扬她的写作。格丽克很早就展露了诗歌天赋,并且对诗歌创作野心勃勃。
十几岁的时候,她比较了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写作,最终放弃了画画,而选择了文学创作,并且野心勃勃。她说:“从十多岁开始,我就希望成为一个诗人。”格丽克提到她还不到三岁,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纵观格丽克的十一本诗集,她一次次回到希腊神话,隐身于这些神话人物的面具后面,唱着冷冷的歌。
格丽克早年曾有自闭的经历,甚至刻意地去绝食,乃至得了厌食症。在十五六岁的少女时代,她就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极端化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也深深影响了她的诗歌创作。
她的过于早慧,让她选择了诗。作家赵松在阅读格丽克的时候,一口气把几本诗集全读完了。“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诗人,是为了写诗而生的人,她选择诗歌作为存在的方式。写诗对她个人来讲是有生命觉醒意味的,这种觉醒不仅是肉体层面的摆脱痛苦,或者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更多的是她找到了某种可能的信仰。”
赵松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格丽克的诗歌不是在强调一种领悟,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想象。她的诗好像是无词歌,她在发出一种声音,词句好像变得已经不重要了,它只是声音的一部分,借助词句的波浪抵达对岸。我觉得这是她的一个最迷人的特点。
诗人、最早翻译格丽克作品的译者之一周瓒对南都记者说:“格丽克的诗歌侧重于从女性经验出发。但又不是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的那种经验,比如受压抑的、痛苦的,或者是一种自白派的、控诉性的经验。她的女性经验涵括了一些很丰富的主题,比如做母亲的经验,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经验,但却不是带有否定意味的、抗议式的写作。她处理的主要是比较正面的经验。格丽克很尖锐,这种尖锐又不是否定性的尖锐,她的尖锐代表了一种很强的洞察力。”
她的诗有令人震惊的疼痛感
“最初读到格丽克,是震惊!仅仅两行,已经让我震惊——震惊于她的疼痛。”译者柳向阳认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而死亡居于核心。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不容置疑。在第一本诗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棉口蛇之国》)
与死亡相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们战胜死亡、远离死亡的现实威胁,就真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安全和幸福吗?格丽克的诗歌给了否定的回答。在《对死亡的恐惧》(诗集《新生》)一诗里,诗人写幼年时的一个噩梦,“当那个梦结束/恐惧依旧。”
在《花园》这组诗里,她给出了“对出生的恐惧”“对爱的恐惧”“对埋葬的恐惧”,俨然是一而三、三而一。由此而言,逃避出生、逃避爱情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格丽克诗中少有幸福的爱情,更多时候是对爱与性的犹疑、排斥,如《夏天》:“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她在《伊萨卡》中写道:“心爱的人/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活在头脑里。”而关于爱情的早期宣言之作《美术馆》写爱的显现,带来的却是爱的泯灭:“她再不可能纯洁地触摸他的胳膊。/他们必须放弃这些……”格丽克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首诗:“强烈的身体需要否定了他们全部的历史,使他们变成了普通人……在我看来,这首诗写的是他们面对那种强迫性需要而无能为力,那种需要嘲弄了他们整个的过去。”
格丽克后期诗歌中,包括青春、性爱、婚恋、友谊……逐渐变得抽象,作为碎片,作为元素,作为体验,在诗作中存在。这一特点在诗集《新生》《七个时期》《阿弗尔诺》中非常明显。更多时候,自传性内容与她的生、死、爱、性主题结合在一起,诗集《阿勒山》堪称典型。
格丽克诗歌的译者之一范静哗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她的诗歌文字是清瘦的,素净的,审美感不是浓郁化不开的抒情,而是冷抒情,温反讽。这样的语言比较难以翻译到位,这与汉语的总体审美取向不太一致。”
她的诗集没有前言、后记
格丽克是如何使用诗的语言呈现“个体”的状态的?柳向阳以《阿弗尔诺》中的第一首诗《夜徙》前两节举例:
正是这一刻,你再次看到
那棵花楸树的红浆果
以及黑暗的天空中
有鸟儿夜徙。
这让我悲伤地想到
死者再看不到它们——
这些事物为我们所依赖,
但它们消逝。
这里“你”与“我”、“我们”的转换令读者不免起疑:这里的人称“你”“我”和 “我们”是泛指的,还是特定的?如果是特定的,指的是谁?柳向阳倾向于认为:“你”“我”对应的是两种身份,两个自我。
她的诗歌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极具私人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这也是格丽克反复强调的。她曾说:“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
实际上,她也一直有意地抹去诗歌作品以外的东西。比如,除了1995年早期四本诗集合订出版时她写过一页简短的“作者说明”外,她的诗集都是只有诗作,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
在中文版出版过程中,诗人也特意提出不要收入。柳向阳曾希望她为中文读者写几句话,也被谢绝了。她说,她对这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她的诗作,此外,让她的照片、签名出现在这本诗选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的好诗人比较多,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格丽克也不意外,从中我们看到美国文化在全球语境中处于有利位置。”诗人黄礼孩认为,格丽克的诗歌能力很强,游荡着学院诗歌的影子,语言很有天分,既准确、到位,又在形象感上游离开来,在语言的意外之处释放出精神之光。她的写作,对诗性的拓展有柔韧度,婉转中有坚定的东西。从自然景物到生活场景,再到宗教层面上的探索,都散发出纯净的气质。
诗人李琬认为:“格丽克的诗行不长,但情感绵密,诗行之间有着骨骼一般清晰且流畅的连接,常常有倾诉的语调,用词简单但色调浓烈,在如今越来越繁复而脆薄的当代生活中,她的诗歌质地唤醒了生活本质中肃穆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