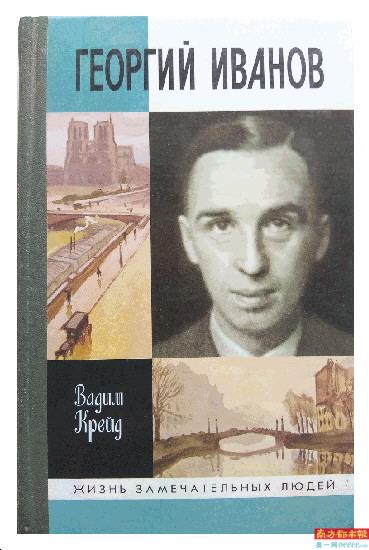
俄文版《格奥尔基·伊万诺夫传》封面。
□ 马海甸
一套丛书在俄罗斯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就是创始于1890年、由图书出版商弗罗伦季·帕夫连科夫主编的《名人传记》。这套以配有人物肖像为特色的丛书原计划出版二百部,后因编者去世(1900年)而中辍。1933年,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国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总领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络绎出版的多部俄苏文学家传记,即以《名人传记》为底本进行迻译。苏联解体后,很多国营出版社如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都随而关闭,唯独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岿然独存,这一选题仍为它的接办人所承袭,同《诗人文库》一样,时代嬗变,仍无改其传递文化之初衷。
当然,这一丛书不能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须与时并进,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求。日前我在两家俄罗斯图书网“游弋”,赫然发现,就在今年,该丛书出版了两部大部头的诗人传记,其一是唯美派诗人阿法纳西·费特传。费特写诗,不大接触现实政治,对民生也少所闻问,专以表现爱情的心理活动和大自然的倏忽变化为能事,托尔斯泰曾在致他的一封信里这样写到:“拆开信件,我首先读到的是您的诗,我鼻子发酸:我跑去找妻子,想给她念一遍;但感动的热泪令我无法读下去。这是一首罕见的诗,不能增益删减,或窜改一字;它本身就是活生生和妙不可言的。它是这样的美好,在我看来,这不是一首偶然之作,而是被堵截良久迸涌而去的第一泓清流。”尽管其作颇得大文豪的赞赏,但在苏联时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还不如李商隐和李贺之于中国诗史。近年费特在俄国学术界行情看涨,这部近五百页的传记,是俄罗斯学术界继两大厚册的《费特及其文学遗产》之后的又一成果。近些年来,有翻译家致力翻译费特,也许,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对较为理想地还原大诗人的作品不无裨益。
其二,是女诗人传记《切鲁宾纳·德·加布利亚克传》,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名字乍一看不像俄国人,但对俄国诗歌史稍有涉猎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诗人叶丽莎维塔·德米特里耶娃的笔名。书厚七百余页,对于一个只活了四十一岁、诗作也不多的诗人,何以传记作者花了如许多的篇幅来挖掘她的一生,不免引起我的好奇。我藏有加布利亚克的一部文集《自白》(《时代象征》丛书之一),2001年初版后就不曾再版。收诗不足百首,诗剧凡二,自传及散文《自白》各一。这位女士在苏联时代消声匿迹,最早提及她的是1989年莫斯科现代人版《缪斯的女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女诗人》一书,但简短的作者介绍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诗名,对诗作特色和成就不置一词。小说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在回忆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文章中曾这样形容加布利亚克的诗作:“她漂亮而动人的诗章是虚伪、忧郁和色情的混合体。”也就在同一篇文章里,托尔斯泰谈到象征派诗人、画家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和古米廖夫为她而决斗的轶事。这一插曲不但令两位斯文人如好斗的公鸡,而且由于事涉众多白银时代诗人如安年斯基、马科夫斯基及库兹明等等,在当时成了一件大新闻。
本世纪新版诗人传与旧版的最大不同处在:前者以白银时代诗人为主,全部新写,有的还出了不止一部,如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已各出两部。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两传尽管略嫌单薄,却是填补空白的新著。勃留索夫(2006)、格奥尔基·伊万诺夫(2007)、赫列勃尼科夫(2007)、梅列日科夫斯基(2008)、K.P.(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的笔名, 2010)、勃洛克(2012)、霍达谢维奇(2012)、萨沙·乔尔内(2013)、库兹明(2013)、索洛古勃(2014)、克留耶夫(2014)、巴尔蒙特(2014)、尼古拉·古米廖夫(2015)、谢维尔亚宁(2018),从这个可能未尽齐备的书目来看,排得上号的白银时代诗人已基本立传。黄金时代的诗人传记,由于上世纪已有多种著作,故而新著不多,仅有维亚泽姆斯基(2004)、巴拉丁斯基(2009)、巴丘什科夫(2011)、丘特切夫(2009、2013)数种。苏联诗人(以殁于苏联解体前者为准)的传记,有鲁布佐夫(2001)、沙拉莫夫(2012)、特瓦尔多夫斯基(2013)、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2013)、马雅可夫斯基(2016)、叶赛宁(2020)五种,后二种苏联解体前有不同作者撰写的同名著作,但对两位诗人悲剧性的结局解释迥异。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曾崛起一批名为“大声疾呼派”的诗人,眼下他们中间最后一位叶甫图申科已于两年前谢世,《名人传记》遂不失时机地推出沃兹列先斯基、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及叶甫图申科四位诗人的传记。俄罗斯诗歌又有“青铜世纪”一说,但与上两世纪各拥有十数位诗人不同,它仅有布罗茨基一人,丛书于2011年出版洛谢夫著《布罗茨基传》。
以上数十种传记,是就传主的贡献(诗歌创作,但他们不一定是职业诗人)而论的,它们的数量不但多于作家、艺术家,而且也多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见过去人们经常引用的叶甫图申科那句诗:“在俄国,诗人不仅仅是诗人”殆非虚言。可惜的是,这些传记已译成中文的仅一部,即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人们往往舍难就易,于是一窝蜂地重译。我不反对必要的重译,但在某些重译已近乎滥的情况下,出版家和翻译家们何不改弦易辙,把更多资源用于移译诗人传记和研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