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人作家张惠雯,现居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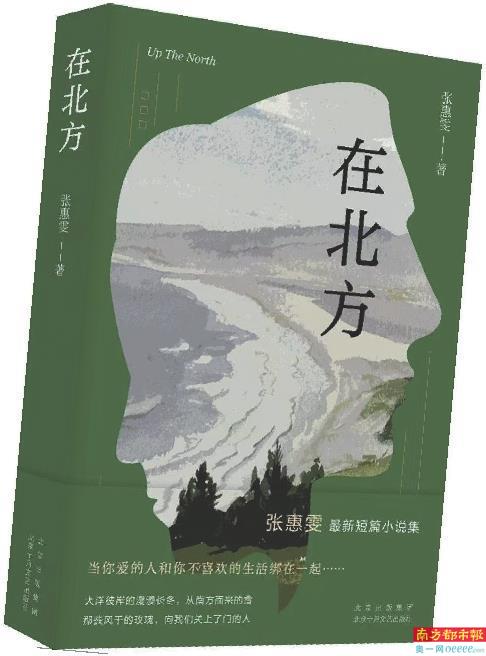
《在北方》,张惠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因篇幅关系,张惠雯访谈全文见报有删节,请扫码读全文
翻开张惠雯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在北方》,辽阔、冷冽的美国新英格兰画卷扑面而来,与此伴随的,是定居于此的华人中产令人嗟叹、回味的人生故事。
张惠雯居住在美国波士顿郊区,是一名中产妈妈、家庭“主妇”。同时,张惠雯也是一位严肃的写作者。她佛系又专注,耐心且勤奋,自言家庭和生活两件事“平衡得还挺好”。
旅居海外近三十年,是写作让她保持着与故乡的血脉连接。迄今为止,张惠雯已出版了《两次相遇》《一瞬间的光线、色彩和阴影》《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在南方》《在北方》等数本小说集。
她的书中惯常出现的,是已无物质之虞,却有心灵之忧的海外华人中产群体。2023年6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在北方》,聚焦于生活在美国北方尤其是东海岸的新英格兰华人移民的生活,包括《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沉默的母亲》《黑鸟》《玫瑰,玫瑰》等九个短篇,均为近三四年间的创作。
谈及整本《在北方》的主题,张惠雯说:“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女性,主要写女性在各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困难、矛盾和心理斗争,以及她们要做的艰难抉择。尤其是行到人生中途的女性,如何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想法,不被这些复杂的关系所碾压和操控。”
因为真实的细节和微妙的心理刻画,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很能引起读者共鸣。她们或者是母亲——被孩子剥夺了整个世界的母亲,丧失经济权利的母亲,在水族馆精疲力竭的母亲,因心理疾病自杀的母亲;或者是恋人或妻子——她们难以在两性关系中被公平对待,有的选择隐忍一生,也有的果断抽离。
这些故事没有激烈的冲突与奇崛的反转,如潺潺流水娓娓道来,却在语言的经营,通篇的节奏、气息和气象方面更接近于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辨识出张惠雯的文字本身所承载的乡愁。他说:“最早的时候,很多海外华文作家凭借比较浅表的题材新鲜感吸引读者,而惠雯的《在南方》已经涉及比较深入的美国社会问题。随着聚焦地区的转移,《在北方》的笔触显得更为严峻、尖锐,或者说是忧伤,这种变化或许与她进一步深入思考女性命运有关”。
专访
反思婚姻中的问题,但并不否定它
南都:《在北方》里的小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新英格兰苍茫、凛冽、具有精神性的自然风景。你认为风景之于短篇故事的作用是什么?
张惠雯:“具有精神性的自然风景”,我喜欢这个描述。新英格兰地区出思想者、诗人,爱默生、梭罗、艾米丽狄金森、洛维尔、弗罗斯特、伊丽莎白毕晓普、希尔维亚普拉斯,包括近年的诺奖得主格丽克……我觉得这和它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的。这个地方风景如画,有大面积的森林,众多湖泊、溪流点缀其中,而且四季变化鲜明。这些东西都会微妙地作用于人的心灵。总之,你会对动植物的生命、景物的变化更为敏感。
通过景物描写达到某种效果,我大概是从俄国小说里学到的。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擅长写风景。但要明白小说里的景物描写是服务于人和故事的,它的作用在于构造一幅人在其中的画面,用景物、氛围烘托出人的精神,并且使这画面留在读者脑海里。
南都:《二人世界》和《沉默的母亲·水族馆的一天》,写到生育对女性身心的巨大改变以及“丧偶式育儿”的困境。“全职妈妈”这个群体常常被屏蔽于社会主流话语之外,但她们的经历和心理状态特别值得作家去挖掘和书写。《二人世界》和《水族馆的一天》里的育儿细节特别真实,其中是否有部分来源于你的个人经历?
张惠雯:肯定有部分细节来源于自己的育儿经验。对于养育孩子这件事,没有亲身体会,基本无法描述出真实细节。这一点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我以前认为好的小说家可以通过观察、共情来准确描述一切自己未曾经历的。但我后来发现唯有在生养孩子这件事上,除非你经历,否则你就无法准确描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男性小说家写恋爱中的女人写得很好,却几乎没有成功描述过女人生养后的内在变化。
不过,我肯定不是这些小说的原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原型,但每个生育过的女性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南都:《在北方》里的许多篇目(包括《玫瑰,玫瑰》《二人世界》《黑鸟》《朱迪》等)都写到了婚姻对女性的约束和捆绑。你怎么理解婚姻、家庭之于女性的意义?据你观察,美国女性对待婚姻、家庭的方式和华人女性有什么不同?
张惠雯:婚姻的“约束”不仅仅是对女性,男女在婚姻里都会有约束和妥协,但在我们的社会,女性往往付出更多。我不反对婚姻,也不反对不婚,究竟哪个选择更好?这因人、因具体情况而异。我感觉对女性而言,好的婚姻有两个前提:它是基于爱的,哪怕是基于友爱;女性在婚姻关系里能获得尊重和平等的权利。
我经常会反思婚姻中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我否定婚姻。我的不少女性友人读了《二人世界》《沉默的母亲》,都极有同感,她们经历过同样的、难以言说的困难和挫折,但这些朋友又都是深爱孩子的、很负责的母亲。所以,承认自己曾疲惫、沮丧,这和爱孩子、承担责任并不矛盾。令女性感到失望的是其他人不愿倾听、理解这些问题,有的男性甚至是“孩子那么可爱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样的态度。正是这种武断、无知、拒绝理解和倾听的态度,迫使母亲们沉默,迫使她们不得不独自处理产后的巨大身心变化带来的痛苦和不适。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为了表现出一种激进姿态而假装是婚姻的蔑视者、受害者。相反,我喜欢那种长期稳定的相伴关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股温暖而坚实的力量。此外,婚姻给予我另一种自由,譬如不坐班、不为生计奔波的自由,使我能在一种较为安定的状态下写作。这听起来很实际,但很重要。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算是婚姻的受益者。
我认为在婚姻关系中的美国女性比中国女性更易保留自我和自尊,也就是说,对于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她们委曲求全的可能性更小。举个例子,在美国,一位家庭主妇离婚后会得到赡养费,这不是指给予孩子的那部分赡养费,而是属于她自己的,因为美国社会认为,女性为照料孩子和家庭而放弃工作,男性和社会应给予其补偿。在此,我们要厘清一个逻辑,这个逻辑不是说女性就理应为家庭牺牲,而是说对于自主选择照料家庭的女性,社会肯定她们的付出,并充分保障她们的权利。这里还有个女性选择权的问题。
在母语写作中接近精神故乡
南都:请讲讲你的写作生涯。你1995年赴新加坡留学,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读大学期间,你就获得了新加坡的多个文学奖项。最开始是什么促使你提笔写作的?又是什么让你持之以恒地写下去的?
张惠雯:这要从小时候说起。我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书籍,幸运的是有个哥哥,比我年长十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典型的文学青年。他买了很多书,到了我能够阅读的年纪,家里已经有了一整架书,有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西方文学,还有一部分哲学、社会学书籍。而且,家长也开明,书架对我完全敞开。我小时候最喜欢读古典诗词。初一以后,开始喜欢读西方文学,先是读现代诗歌,后来扩展到小说,读了不少古典小说,譬如司汤达、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中时这种阅读基本中断了。但后来去新加坡读大学,又重拾了阅读的兴趣。读多了,免不了会想到自己动笔写,所以我觉得年少时的阅读已经埋下了写作的种子。
不过,除了阅读的铺垫,其实还有个“契机”,就是突然到了异国他乡的“乡愁”。由于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语,我当时就突然进入了纯英文的学习环境。结果我的思乡病就不仅是思念故乡、亲人,还有那种被迫和母语“分离”而导致的对中文、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我当时仿佛有种逆反心理:你越让我和她(母语)分离,我心里就越要和她亲密。于是,我找到的排解乡愁的方法就是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古柳官河》。我在使用母语的写作中接近了故乡,找到了慰藉。
能持之以恒地写,就是因为我的动机极其单纯:因为喜爱而写。只要这种爱还在,就会一直写下去。
南都:长年居住海外,你怎么和母语以及中国文化保持必要的关联?隔开一定的时空距离,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新的认识?
张惠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通过用母语来写作,这是我接近故土的最好的方式。隔开一定的距离,我觉得更能看到传统文化中的问题,但对于其中美好的部分,也会更觉向往、亲近。
南都:请谈谈当下的写作和生活状况。
张惠雯:生活方面,我是位母亲,也是一位主妇,要负责家里的采买、一日三餐等等杂务,也要给孩子足够的陪伴。其余的时间,我可以自己支配。目前,我的家庭“工作”和写作二者平衡得挺好。
我写作比较随性,没什么纪律性,更没有每天必须写多久、什么时间写这一类的固定安排。有时,我两三个月内可能连续在写,但有时三个月也不写一个字。不过,我每年总会写出三四部短篇。我不在意速度或数量,但不允许自己把写作“搁置”太久。我觉得作家或者“在写”,或者“在读”,或者在为写作做着其他准备。即便你在街上闲逛或是和朋友闲聊,你可能都在为写作做准备,这大概就是福楼拜所说的“为写作而生活”吧。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