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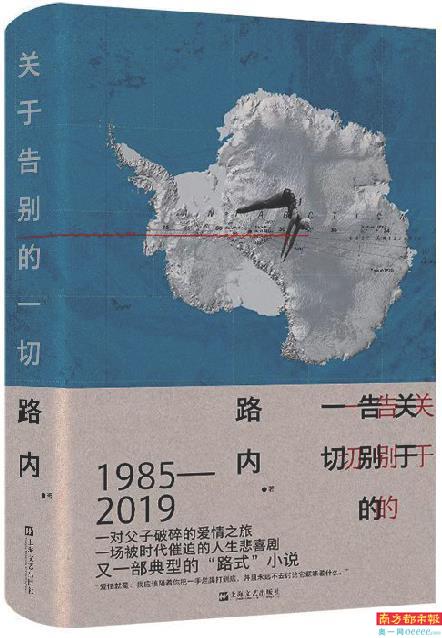
在写《关于告别的一切》期间,路内的豆瓣账号改成了“Lee Bah”(李白)。此种移花接木手法,很有些佩索阿的意味。李白身上影影绰绰也有路内本人的影子。这部小说从1985年写到2019年,从小镇作家李白的少年写到中年,路内说:“应该是中年部分我借着他讲了一些话”。
这是继2020年《雾行者》出版之后,路内推出的又一部长篇新作。标准的“路式”风格重现:意象密织、语流湍急、气氛飞扬欢脱。由于主人公是一位十八线小作家,“谈过十几场恋爱,写过两三本书,长篇小说《太子巷往事》曾入围陈量材文学奖”,对话中还总杂糅着萨特、弗洛伊德、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诡辩与饶舌。以泥沙俱下的复杂腔调,路内记述了吴里小镇的李白和李忠诚父子三十多年的人生欢愁。
“告别”这个动作是从李白9岁那年,母亲白淑珍离家出走开始的。从那以后,它就像一个符咒,将李白推入一场场有始无终,有时候比露水还短暂的恋爱。他既是情痴又是浪荡子,既背叛又被背叛,声言“爱情就是:我应该陪着你把一手烂牌打到底,并且永远不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
听起来狡黠而动人,一些读者将李白盖章认证为“暖渣”。路内说:“他的问题不是不忠贞,而是认识到了忠贞是一种由诸多历史条件构成的结果,而善良是一种不需要历史来认证的品性。”
虽然爱情是小说里十分抓眼的元素,但这部小说本质上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文学的永恒母题——时间。和初恋曾小然的重逢开启了时间的回溯模式,“重逢犹如单行道上的车祸,往事接二连三追尾。”
正如文学评论家程德培所言:“《关于告别的一切》展示给我们的是热情的记忆,痛苦的不堪回首和随意挥洒的语言混合,是在雪崩似的大量联想、甚至议论中重获的时光。”你会在阅读当中以N倍速重温那些年代,仿佛拥有了某种双重的时间或生命体验。
所以告别也是与过往时间的告别,是对生命、青春和激情的叹逝。路内说:“我把告别看成是一种朴素的仪式,古今皆同,是万古愁,但也没有很愁。”“告别放大了遗憾,也可以消解遗憾”。就这样一边解构一边建构,一边告别一边奔赴;一边破碎一边完满。
访谈
这是一部故事好笑的小说
南都:写《关于告别的一切》这本小说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一本以“告别”为主题的小说?你怎么理解生命中的告别这件事?
路内:这是一部故事好笑的小说。上一次写这种类型的长篇,是《天使坠落在哪里》,八年前出版。其后的两部,都比较严肃。我也是心心念念,总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叠加并且推翻些什么。时隔八年,每个人的认知都变了很多。故事发生的场域又回到了江南地区,这说明“好笑”的小说难写,很正经的小说可以放在我略为陌生的环境。两者的提取方式有差别。
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叫《南方饮食》,我觉得更轻快些,告别只是其中的主题之一。写着写着,告别变重了,“一切”是个更重的词。我似乎理解到,这有点像具体的人生,其中含有哀愁。但这哀愁是珍贵还是廉价,珍贵的是否应该写,廉价的是否值得写?我觉得“为什么写”很难解释。我愿意像初学者一样,由一个任意的主题来剖开事物表面,而不是纠缠于主题,那是成熟编剧的事。
我把告别看成是一种朴素的仪式,总有人要站起来告辞,去别处接受邂逅和重逢。告别放大了遗憾,也可以消解掉遗憾。
南都:小说主人公李白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小镇作家,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你在小说出版前把豆瓣用户名改成了Lee Bah,李白身上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
路内: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我也有点。就是表面上轻率,好打交道,但在特定时刻会十分难搞。心情不好很桀骜,但也坚持不了太久的那种人。中年以后,他们会反思自己的轻率和桀骜(姑且指男性),和人格做一些抗争,但好像也坚持不了太久。我要问问心理医生,这属于什么情况。
我的习惯是把豆瓣账号改成正在写的主人公的名字,这意味着,该账号不是官方发言,不代表“路内这个写小说的人”。很矫情是吧?主人公李白身上当然有一些我的影子,谈恋爱是借了别人的故事。这小说的时间轴有点长,从少年到中年,应该是中年部分我借着他讲了一些话,前半部分受小说技术的约束,后半部分,我和人物共同讨论了一些问题。
南都:《关于告别的一切》整体上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李白的“我”经常跳出来讲几句,有点像内心独白,于是小说看起来有两个叙述者。这在文体上是比较奇怪的。你能解释一下这种写法吗?
路内:也不算是特别有突破的写法,只是一种叙述上的尝试,有点像话剧,故事演着演着,人物忽然对着观众独白了。如果这么理解的话,这小说的整个故事背景都是虚的,也像话剧的布景。那么,在我看来,把这故事放在哪个城市,区别不大。它可以抽取出一些有意思的话语,把一个故事(或者把它理解为一个段子,一次经历,一场人生剧)表现得更好,更有现场感。它可以抵消掉小说中的回忆气息。
如果很凌空蹈虚的话,它会变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个表现法,但对写小说的人而言,我并没有一个舞台、一束光线和两个演员作为观看的载体,我只有文字,要凌空很难。这个手法影响了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导向。比如说,故事偏于日常,悬疑肯定是不行的,会散架;人物有一点漫画,导致人物关系薄了,需要用其他方式去补足。
我这个说法复杂了。希望在故事的表现上能更好看,更有叙述韧性。这手法确实不适用于所有格式的小说,以后再写的机会不多。
主人公被读者盖章“暖渣”
南都:李白的母亲白淑珍的离家出走是他一生当中“告别”的开始,也是难以弥补的童年创伤。后来他的生命中来来往往许多女性,曾小然、周安娜、钟岚、张幼苹……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试图留住任何一个?他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潜意识的惯性?
路内:是他留不住,也就放弃这种努力了。相反他还会嘲笑好友冯江,是一个对新情旧恋和婚姻同时保持着无度狂热的人,令李白打了个寒战。他的问题不是不忠贞,而是认识到了忠贞(还有其他,比如伟大)是一种由诸多历史条件构成的结果,而善良是一种不需要历史来认证的品性。如此一来,用一些读者的话,“暖渣”就是这么出品了。
这个说法用来解释爱情,尤其自己的,很像借口。小说里提到过一句,说他的根本错误是“把面相学当成了解剖学”。三十六岁以后他是从这种惯性中解脱出来的,小说被有些人说“中年花心”,不是的,他根本就是青年花心。
南都: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李白发现外公和母亲有可能从事特工工作,读到这里原本以为会出现神反转,结果并没有。写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呢?
路内:既然他不承认历史构成的前提,那么历史也不会给他一个所需要的答案。如果承认了这个前提,就要接受一切既定的答案,他不能选一个自己想要的,更不能自己去解答。这件事算是根本意义上的残酷。
我这么说太曲折了。这可能不是针对人生的残酷,而是针对文学的残酷。退一步讲,虽然他没有获得真正的答案,但他靠想象和推理(其实就是胡抡)认为母亲并没有跟着大款去南方,而是跳出了陈旧的女性符号,去做了一件并不存在于人世的事情。这也算是对他的安慰。
使用了一种繁复混杂的语言
南都:小说里有人批评李白“你这种在街头巷尾找素材的作家才是低级的”,还有一段叙述者的话,“他们被迫写自己的三亲六故、闾里见闻、情史性史,被迫展现小镇风貌……”你觉得作家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寻找素材?你自己是怎么保持写作的生命力的?
路内:这段好像是自嘲。我经常被评论界认为是小镇作家,其实我是地级市户口,写的也基本是地级市。这个说法真的很庸俗,但放在文学中,它偏偏构成了一个流派的定义。小镇作家跟小镇做题家听起来太像了,部分网友分不清这个,直接把前者打进鄙视链低端。他们居然与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合谋了,就是作品要广阔、伟大。
当然,伟大的小说和伟大的素材,是可贵的。素材无非是经验、听闻、阅读,没有哪个方式是更优的。我的个人看法是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现实题材的小说素材更难得些。个人经验变得像点金石一样重要,经验同时也是有限的、容易同质化的、带有欺骗性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保持写作生命力的,我设定的写作计划还没完成,得向那个方向走。
南都:这部小说在语言方面,写作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和设计?
路内:当然设计过。以前写的题材,没法用上一种繁复混杂的语言,追随三部曲还是比较口语化,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主人公是同行,半吊子都市知识分子,不纯粹直男,半真不假地讲点日常的真事。这个调性(还有它所表达的事物)是否有文学价值,是要试过以后等评判的。
南都: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可以一直地写下去的。你写到什么时候觉得小说可以结束了?为什么把结尾安排在动物园的熊山?
路内:过分强调叙述语调的小说会达到一个极限,因为故事散文化了,看上去可以无限扩展,但一定会在某个位置上突然断裂掉。得在厌倦来临前结束掉它。也许有人已经厌倦了,他就会打个二星,这我同意。人们还是更信得过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就算读不完也是好的,但对当代作家没这么宽容。
动物园是一个早就想写的场所,在那里,动物是人的拟态,你不要笑我乱用词,以后我要好好写一本动物园小说。至于结尾的寓意,还是请交给文本分析家吧。
南都:程德培说你是小说领域的“年鉴学派”,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评价?哪一样是你小说中真正的主角,时间、人物还是故事?
路内:过去那些年,写的小说有很多都是长时间轴的,被这么评价很惭愧,长时间轴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学的“年鉴学派”。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写好。诸多要素都无法高于小说本身。有时我也被要求谈论自己,仿佛自己才是小说中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这样。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