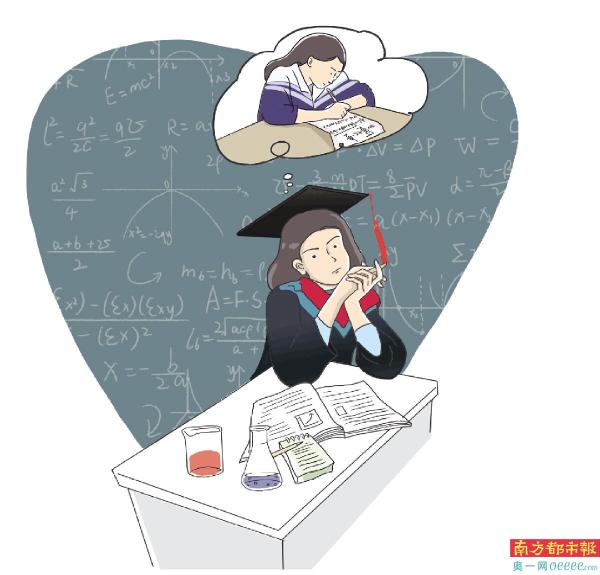
那日晚饭时,先生说到自己公司的一个同事,年轻时候有个学术梦,坚持了八年科研,最终因为终身教职遥遥无期,选择了离开学界,进入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福利和薪水都很不错,33岁终于稳定下来,不用再和博士后时期一样每三两年就得挪窝。他却对先生说,稳定是好的,只是还忍不住会怀念做研究的那些日子。
听完他的故事我失神了好一阵子,这两年因为工作孩子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停下来梳理一路走来的历程,却不想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了共鸣,这些年从坚持到放弃的科研经历,像潮水一样涌入脑海。
为了数学梦去法国读博士
我爱数学,直至今日都会因为一个美丽的定理惊呼数学之美。在国内读本科,四年数学生涯,我无一例外每日清晨等读书馆开门,等到夜深了才回寝室休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是一名优秀的数学教授。因为费马、欧拉等让我高山仰止的数学伟人都来自法国,我决定去法国做数学博士。三年博士,两年半博士后,我花了五年半的时间一门心思投身科研,只为了实现大学本科时就开始的梦想。
除了科研,我也在博士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先生,他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一起做论文。两人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细水长流就走到了一起。我的先生书生气十足,眉清目秀,性格也与我合拍。唯一可惜的是,他是法国人。我从未想过远嫁他乡,却终抵不过爱情的力量,决心与他一起留在法国。因此在法国找教职,成为了那些年我人生的第一大目标。博士毕业近四年,如今的我却远离当时的梦想,在一家私企工作,过着朝九晚五、上班编程下班带孩子的生活。
前不久和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聊天,我说我如今在何处工作。他问我:“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学?”我说:“那里没有大学,我在一家私企工作。”他一下子就惊了:“你,私企?怎么可能?”我性格安静,喜欢一个人坐很久思考一个数学问题。有一回去看病,等得久了,我就拿着自己的病历本算起了方程,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画满了半本病历本。
刚准备放弃科研的那会儿去找工作,人事跟我说,你太安静了,我们公司不适合你。可就是这样,我还是放弃了科研。
为了拿教职在法国德国两度做博后
博士期间,我在世界排名未曾掉出前三的顶尖大学顶尖实验室顶尖教授手下写了300页的博士论文,发了4篇顶尖期刊的文章,自信满满地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尽快拿到一个稳定教职,在大学里研究授课。
博士后第一年,我进入了一个数学研究团队。团队的老板跟我说,你好好写文章,多发文章,一定可以找到稳定教职。于是我没日没夜地写,即使去度假,坐大巴,买票排队时也在思考可能根本没什么用的科研问题。这一年年末,我发现自己怀孕。这个孩子的到来让我更坚定了自己早日稳定下来的目标。很遗憾,这个孩子流产了。不久后,这一年的终身教职申请失败。
随后,这个博士后接近尾声。团队的大老板跟我说,你的能力很好,但是你缺乏国外博士后的经验(我的博士和第一个博士后都是在法国做的),这样吧,你去德国,在我们同一个团队的另一个老板手下做。有这个经历,你一定能拿下终身教职。
如今回想起来,这未必是老板对我的肯定,也许只是一个让我继续为团队贡献力量的说辞罢了。但我就因为他说的“一定”,坚定地踏上了去德国的路。上火车的那天,和丈夫新婚未满四个月。之后的一年半异地生活,只是靠着一个信念“努力科研争取拿到教职我们就能稳定下来”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这期间我流产了第二次。去医院检查了多次,医生只说查不出原因,只是因为胚胎质量不好、优胜劣汰罢了。但第二个孩子的离去让我心态崩溃,第一次对自己曾经的信念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我开始用围城外的眼光打量学界
又一年法国教职的评选开始,我联系了各大实验室研究所,有不少人表现出了对我的简历颇有兴趣,请我去演讲交流。交流后,无一不表现出了对我的兴趣。我志在必得地申请这些实验室研究所的教职,觉得至少能得到三五个职位的终身名额,但却无比可笑地全部落了空。最后的名单上,不敢说全部,我觉得至少有一半的最终候选人简历远不如我。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申请的最后一个实验室出结果的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散步,最终筋疲力尽,坐在一张周围人流不息的长凳上,只觉得自己可笑。我还自恋地觉得别人对我感兴趣,别人或许只是请我去做个样子,让大家觉得他们的评选公开透明。
次日,我稳定了情绪,去同事兼好友莫森的办公室和他聊天。这些年来第一次,我完整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除了先生之外的人听。莫森说你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奇怪啊,我的师傅今年35岁了,依然没有稳定教职,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间颠沛流离,顶尖期刊20来篇,到头来还不是输给了只有两篇文章的小朋友。你以为学术能力强就等于找到职位?不懂江湖规则了吧?还有,你真的觉得学术很了不起吗?多少人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不是为了寻找真理而学术。每年arXiv上那么多文章,有多少是真的有价值的?自我感动罢了。
这次谈话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可笑。科研不过一个工作而已,我却把它看得这么崇高。刚好那个星期数学所邀请一个副教授来做讲座。讲座结束的时候莫森问他:你这个算法有什么实际应用?他一下子就很生气,巴拉巴拉地说大概我在跟你讲数学,你跟我说什么应用?有种神仙姐姐不屑于下凡的感觉。那一天,我用围城外的眼光看学界的很多人,我发现我完全理解不了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动。
老板没能说服我,我提交了辞呈
一旦开始用这种眼光打量学术界,我就看到了不少从前看不到的东西。
数学家丘成桐的书里讲学术界的恩怨,说有人领地意识很重,觉得我的学术领域即是我的领地,他人做了我的课题,便是入侵者。他甚至说到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恩怨,可见即便是最顶层的教授们,也并非人人纯粹,以真理为目的。
我博士期间的好友Y同学写了一篇论文,但不久后收到该领域大佬D先生(此人当时已经是剑桥的教授)的邮件,说“你写的是我的领域,你要是敢发表,我要你好看”。他和我聊起这件事的时候颇为感慨,说有学术梦有什么用,人家可不允许我们随便做梦。
教职评选彻底落空后的第二周,我把自己博士时开始的工作都拿出来仔细读了。这一次,我用的是一个不懂数学的人的眼光。这些有什么用?我问自己。没有答案。
一来找不到出路,二来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昔日坚定如我,也终于决定要离开。去找老板聊天,他自然试图说服我留下来。我说我已经做了两年半博士后了,很累,想走了。他跟我谈了很久数学的美好,要我坚持自己的梦想。他劝我,说进入企业就是在浪费自己,玷污自己的数学背景。我说我累了。他说你可以走,但先把手头的文章给我写了。哦,我想了想,也许你只是想用这些说辞来挽留一个很会写文章的PhD吧。即便你是诚心的,我也理解不了这些了。我爱研究,数学真的很美,可是科研的江湖不是一潭清水。
老板没能说服我,我最终提交了辞呈。之后的日子,我给自己放了个短假,回到先生租来的单身公寓里。奔波这些年,我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个躺平的机会。有一天下午忽然倾盆大雨,放晴后天边一道彩虹。我觉得自己被锁死在一个执念里太多年,也许彩虹的那头,是另一个世界呢?那天下午我投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简历,给一家科技公司。
数学也许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找工作的经历漫长,毕竟一个熟悉黑洞流体偏微分的数学博士在实业公司面前,就是一个超级小白。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自学人工智能的知识,立志成为一个数据科学家——这是一个市场需求很大而离我专业知识不太远的职业。从零开始的自学过程极为辛苦,但我依然成功了。看到彩虹的那天下午,我怀上了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如今一岁,摇摇晃晃会走路了。我们有了自己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日子平静安宁,我虽不再科研,却依然觉得平实满足。
不久前和硕士期间的好友馨聊天。馨博士后毕业留校,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处学术界最底层。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却像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博士期间的剩余价值基本被老板压榨完,难以出新成果,恐怕下一轮考核无法完成,要被辞退。馨说真羡慕你全身而退。她问我离开一年半以来有什么感想。我说如今生活得很好,压力没有以前大了,发量也增加了,能够扎丸子头了。但仍放不下数学,于是每天早起上班前以及下班后带娃的空隙都会看大量新的理论,也会花大量时间思考,不以发表考核为目的,更能体会到数学之美了。
当然,我还是很怀念科研的日子。但我觉得怀念的只是个人想象里的那个没有江湖险恶的学术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和我做什么无关,数学也许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Charlotte (数据科学家 现居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