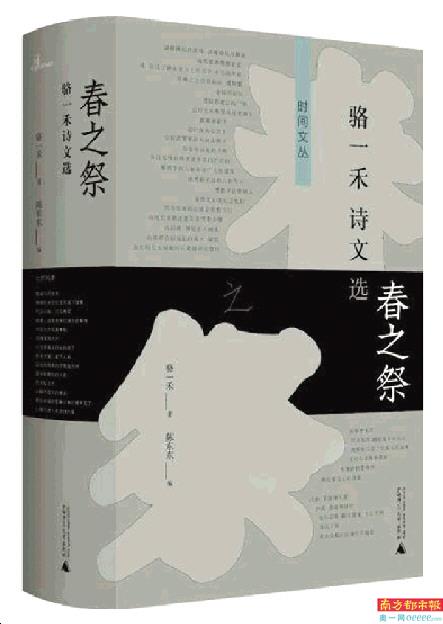
《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骆一禾著,陈东东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诗人骆一禾(1961-1989)生前与妻子张玞在华山。
□ 陈东东
已经有许多人谈到了骆一禾对海子的影响。在跟诗人徐钺对话时,西川说:“骆一禾广阔的关怀对海子我想其实是有影响的。海子就开始思考这种广阔,比如海子的《土地》里就开始有结构了……”燎原在《孪生的麦地之子》一文里对比过骆一禾与海子的一些诗句,让人从一个方面比较直观地看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启发和引领。骆一禾的妻子张玞以其跟骆一禾生活的密切和观察,“觉得一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海子的老师。”在十年前的一次讨论会上,她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的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然后海子诗歌受打击的时候,一禾也跟着去分析他的诗歌、朗诵他的诗歌。一禾和海子的关系,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一禾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感动,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老木(跟骆一禾是北大中文系的79级同学)在哪里看到了这段话,三年前某一天给我发短信说:“……想请你补正一下,当年是我把海子带到骆一禾面前的,我介绍说这是个天才。可惜了二人都英年早逝。”发这短信的时候,老木才被人从巴黎街头找回来没多久——在张玞参与的那次讨论会上,宋琳、孙文波、西渡、姜涛、秦晓宇、冷霜等人也都讲到了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这两位诗人共同的精神背景、密切的交往,相互激发和大方向一致的写作。
1989年3月底和5月末,海子与骆一禾先后辞世,6月15日,我写了一篇悼文,刊于当年9月号的《上海文学》,其中有言:“……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在海子和骆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练和提升了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化得越来越悦耳……”当年这么说的时候,我对骆一禾、海子之间的事情了解得并不太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骆一禾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处理突然且暴烈的海子之死的那种全身心投入——我在上海,经由骆一禾、西川,及后来张玞的北京来信,能够感同身受——骆一禾说:“海子的死讯像一捆镰刀射上了我的肝胆……”可想而知,这打击对他有怎样的摧毁力!他立即与海子的家人、中国政法大学(海子工作单位)的人一起赶赴海子出事的地点山海关。从山海关回来,骆一禾未回家而先去了西川和邹静之那儿,他俩后来回忆,骆一禾一脸疲倦,头发上、黑色的风衣上落满尘土。
骆一禾1989年4月21日的来信(我留存的唯一一封他的来信)报道说:从山海关回来后,他忙于海子的后事直到4月10日;然后立即投入海子浩繁的遗稿,很快大致整理出长诗部分;其间又跟几家杂志报纸商定海子的纪念专页;找出版社争取出版海子的诗集;搞义捐活动;4月7日,他在北大组织海子的纪念朗诵;4月11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海子的写作“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那是一种持续劳碌的节奏——从他留下的几篇有关海子的文章,也能看到他透支脑力体力的紧张状态:4月12日凌晨,写成三千多字的《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4月26日,写成近六千字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5月13日,写成近三千字的《海子生涯》……他急于让人们去听见海子,像他那样去倾听——这种急切大概从他认识海子不久就开始了,除了常常在朋友们中间推荐和讲述海子,在书信和文章(不唯他在海子死后撰写的那三篇)里批评、分析和研究海子,骆一禾在《十月》杂志开设的“十月的诗”栏目也大力展示海子,栏目从1987年第一期开始,到他病逝之前,出刊不到三年,其中就有三期大篇幅发表了海子的诗作……骆一禾贡献给人们一个他所辨音的海子,一个他整体性地把握、勾勒和塑形的海子,其细致清晰,表明那是长期注重和思量的结果。就像诗人姜涛说的那样,这“为理解海子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日后关于海子的解说连篇累牍,精彩的见解也层出不穷,但没有哪一种说法真的能摆脱这一框架。”
所以,在面对三十年来海子愈益热门,(夸张一点说)海子光辉的诗歌迅速广被中华,以至名满天下的景象时,人们应该会注意到骆一禾对海子的影响——人们不能不看到骆一禾曾倾其全力对海子诗歌的整理、评介和推广;人们也不能不意识到,这其中正好包含着骆一禾对诗歌格局、写作方向的看待和设想,正有着对他自己的某种阅读期待。在三十年前的那篇悼文里,我认为骆一禾优异的倾听之耳跟海子的歌喉仿佛有一种对应关系,紧接着我说明了那么讲的语境:“一禾有同样优异的嗓子,然而其倾听犹为可贵。他谈论的始终是他的倾听,他愿意让其他耳朵与他共享诗之精髓和神的音乐。一禾的这种优异,集中于他对海子歌唱的倾听。当一些耳朵出于不同的原因纷纷向海子关闭的时候,一禾几乎是独自沉醉于海子的音乐,并且因为领悟而感叹。”二十年后,在重读骆一禾诗论的一篇文章里,姜涛敏捷地一语道破:骆一禾的“倾听”应被“看作一种主动的、伴随了创造性颖悟、强劲有力的命名,那么所谓‘歌唱’与‘倾听’之间的关联,仍是讨论骆一禾诗歌遗产的一个起点。因为,他优异的‘倾听之耳’,与其说是向亡友孤独敞开,毋宁说是已将后者的歌唱卷入到自己内部某种更大的精神风暴之中。”骆一禾自己,则在写于1989年的一篇题为《火光》的诗论里说:“那么诗歌意识或诗学,对我就不是创作活动之外的,我也就不能同意它们不揭示诗,不作用于诗。我想这也是瓦莱里以及波德莱尔提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综合的艺术思维创作活动(‘沉思’)……”那篇文章一开头,他就写道:“……论述的话语里总存在着另一种吸引力,促使我放弃而投入浩瀚无边的创作活动中去。”
可以说,倾听之于骆一禾恰是创造性之一种,甚至是其写作的过程,是其歌唱的一部分。他的中文系毕业论文《太阳城》将北岛和他自己的诗歌批评观一起谈论,“认识诗流已有的成就,也就是蕴积着一次认识的突破、诗流的突破”(《太阳城》);他浓墨重彩地论述昌耀,“用生动深入的判断力去识别同时代的大作品和大诗人”(《论昌耀》);他在“十月的诗”栏目里揭示他辨认出来的当代优秀诗人,“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为〈十月〉诗歌版的引言》)——它们跟他对海子的倾听是一样的,以其“从纵深看过去的眼力”提供“认识价值,而许多新艺术之初都未必易认同而又分明是可认识的”(《冲击极限——我心目中的海子》)。当骆一禾在给友人的信里写下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的时候,当他说“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觉得“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的时候,并非没有一种非凡的听力在起作用。他最为重要的,试图创立其“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的《美神》一开篇即关乎倾听:
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像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谛听着大地与海洋的搏斗,风雨雷电、黄昏和火阵、我的伴侣、朋友和姐妹们在沉睡中吹息放射,呈现出他们的面颊、手艺和身体。
显然,倾听正是骆一禾的意愿,他是那个以自觉的倾听者形象出场的诗人,那个“灵敏其耳”(《修远》)而非“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最少听见声音的耳鼓里/敲响的火在倒下来”(《巴赫的十二圣咏》)的诗人。跟海子理想化所谓“诗歌之王”不太一样,骆一禾以“一个圣者”要求于诗人——看一眼繁写的“圣”字,倾听正包含其中——许慎《说文解字》将“圣”字置于耳部:“圣,通也,从耳呈声,式正切。”灵通开敞、融会贯通的倾听之耳跟西川所说骆一禾广阔的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骆一禾考虑三种时间以确立自己诗歌的志业和使命,叩诊测度旧文明之死和新文明之生终于迈向史诗性写作,正出于他那“河流像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的倾听。
骆一禾这样一个以倾听为核心的圣者诗人形象,却曾经遭受了(或许依然在遭受着)一些误会和轻视。举其一例,譬如,大概因为跟海子身后被大肆传扬、广泛倾听形成某种反差,觉得骆一禾的声名未得过于彰显,一位诗评家在题为《骆一禾:敲响的火在倒下来……》的文章里认为:“如果说新生代诗人中有谁被真正遮蔽了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杰出的诗人骆一禾。”这句话里没有说明是谁“真正遮蔽”及怎样“遮蔽”了骆一禾,但在上下文里,诗评家抱怨骆一禾“被诗歌界只是定位为海子诗歌的‘倾听者’,这种定位一直到今天竟未曾改变。”而“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现代汉诗的历史上,旷日长久地被称为是‘倾听者’,受到如此严重的遮蔽,这不仅是诗坛严重的失察,也表明人心的冷漠与势利,我们谁都没有权力更不应有胆量和心肠再继续沉默下去。”——后面那句真的是重话,于我的感受已接近于打棍子——在一篇悼文里将海子和骆一禾之间的关系比方为“歌唱者”和“倾听者”是否算一种“定位”,是否“严重的失察”,可以讨论;说这“也表明人心的冷漠与势利”,则让人搞不清楚凭的是哪种逻辑,出自于哪股恶气——如果并非别有用意居心,那就只当它是诗评家惯常的一派胡言吧……
称骆一禾为“倾听者”绝无贬低,而是去表明和突出他优异于众人的一种诗人品质。那位诗评家尝言:“对于诗歌写作来说……还有一个决定性的致命条件——我应该直接说吗?——天才。”那么,倾听能力恰是骆一禾之天才的极为重要和特长的方面,这表现在他设计和辨析自己写作的那种超凡的自觉,这也表现在他作为一个好编辑,一个敏锐的批评家为当代诗歌进展所作的贡献。后二者不妨视为骆一禾诗歌自觉的推己及人,尤为突显于他对海子细致的倾听。去做个诗评家,本当具备、信任和推崇高超的倾听能力,不断进化自己的倾听能力使之灵透,以服务于诗歌和诗人;其反而小觑、缩减“倾听”在诗歌写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认定称一个诗人为“倾听者”是矮化行为,起遮闭作用……或许,你只能说这位诗评家的倾听能力实在有限。另外,我不认为非得像海子那样流行起来,诗人才算没有被遮闭——而且我觉得遮闭之说本身就很可疑:遮闭的主语是什么呢?谁又有能力将诗人和诗歌遮闭起来?想一想曼德尔斯塔姆或庞德的极端际遇,那是能够被遮闭的吗?——相反,真要是将某个诗人炒作起来,将之明星化、主流化、普及化,无限消费(包括在传媒、出版、奖项、会议、课堂、批评和研究等方面的过度消费),在我看来,倒是对诗人货真价实的一种抹杀。尽管跟很多优秀诗人在这个时代得到的待遇没什么不同,骆一禾并未被热烈地爱戴,隆重地眷顾,但骆一禾也从未被谁遮闭。昭示海子当然不会遮闭骆一禾或其他任何诗人,而只会让人更多地怀念和接近每一个诗人,所有的诗歌;骆一禾跟海子之间的特殊关联,更使得对海子的注目会让人想起骆一禾的倾听。
经由那广博的倾听而汇成的骆一禾大质量的声音没有消失,不会消失,总是有人要为之倾听。在即将出版的《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文集》的编者弁言里我写道:“这位以文明为背景对写作进行过周密的思量和规划、高瞻远瞩、迈上修远之路的诗人,从未被读者、被同道、被至爱亲朋忘却,他精神遗产的意义和影响,他‘灵敏其耳’‘血流充沛了万马’的诗歌,重要性愈益彰显,那灵魂的形象(就像他曾就海子之死所说)‘依然腾矗在他的骨灰上’”。而在刚刚出版的厚厚一册《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的编者弁言里我说的是:“骆一禾看到‘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并以其写作加入进去。编选和阅读骆一禾,也是为了像他一样加入进去。”
◎陈东东,诗人,作家。著有诗文本《流水》《陈东东的诗》,随笔集《黑镜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