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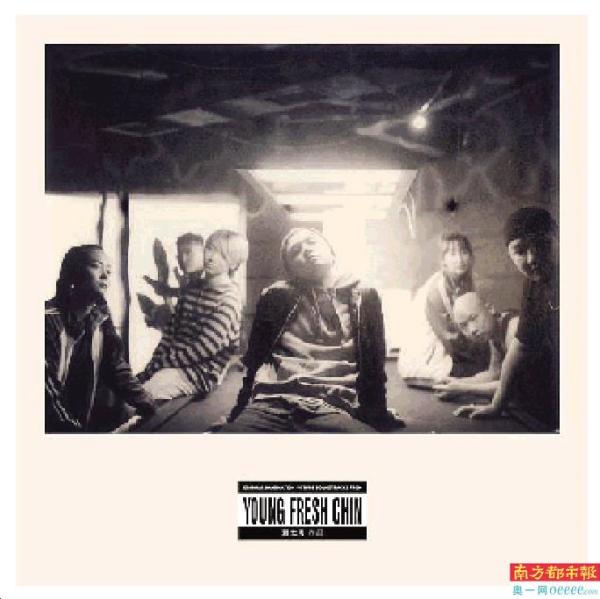

2020年底,成功冲击KPI的夏之禹发了自己“不存在的电影系列”第二部《Young Fresh Chin》,承接第一部《California Dream》,通过游戏厅、街头、爱情等关键词描写小镇生活,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就像采访全程他带给大家的感觉——过了而立之年却依然心怀纯真的浪漫派。
因为《说唱新世代》,更多人认识到夏之禹,充满浪漫想象力与诗意的情绪表达备受乐迷与专业媒体好评,在上节目之前他已经是圈内的“宝藏Rapper”,有被评论认为是纯正的old school,“是中国南方街头说唱,四川古惑仔说唱,浪漫主义说唱”,还有人因为他的纪实色彩称他为“说唱贾樟柯”。上个月来广州参加南方音乐盛典,在接受南都专访时他很正式地说“我不是说唱贾樟柯,我也没有刻意还原某个时代”,他只认自己是一个“社会化失败的浪漫派”。
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实习生 吴倩楠 林汝娉
“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
作为一个Rapper,夏之禹心中真正的hip-hop其实源于学生时期的最初接触。在一首首听不懂的英文歌里,青少年时期的他重塑了自己对于英雄的认知,英雄是有血有肉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南都:是如何想到要做这样一张专辑并且把它作为系列的第二部的?
夏之禹:其实这张专辑包括上一张《California Dream》的初衷都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把音乐做得硬派一点。但是要想一个方式减轻那种严肃和厚重,因为如果整体氛围搞得很严肃的话,大众没那么容易接受。
南都:新专辑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关键词,比如游戏厅,比如街头,是如何在创作中提炼出来的?
夏之禹:我写东西不会去先立一个大纲,所以也没有专门地去提炼,都是跟着感觉走。像《游戏》这首歌,是之前和朋友聊天,大家觉得游戏厅就是一个社会安全阀理论。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新型的娱乐方式,给无处撒欢的年轻人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大门,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就有地方释放了。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写了这首歌。
南都:专辑里面有没有什么故事是你之前经历过的?
夏之禹:亲身经历过的几乎没有,其实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怂的人。但是因为我老家四川广元宝轮镇是三省交界,产业结构比较复杂,流动人口非常大,可想而知它的生活形态会比较丰富。然后那些故事虽然我基本没有参与过,但基本是发生在身边。一个镇可能就几万人,都是互相认识的,所以很多故事基本大家都知道。
南都:之前自己有评价说这张专辑不够完美,是还有一些遗憾吗?
夏之禹: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一个是和斯威特合作的《Ghetto Dream》,其实我本来是想写16岁的主角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要成为这个镇上名流一样的人物,可能开火锅店,可能开宾馆,但觉得没写到那个点上。另外一个是《Young Lovers in Da Hood》,已经有了关于爱情的歌《Hey You》,最后一首不打算再写爱情,是想再写一个大院生活全景的歌,也是写了好几版,基本都觉得不行,就说那就把情歌的主题再延续一首。其实承接得也很好,只是当时我希望最后一首歌给一个全景,没有给出来。这两首歌只是说跟我原先想要去描写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总体这张专辑还是还原了我心目中real hip-hop的样子。
南都:心目中real hip-hop是什么样子的?
夏之禹:最开始接触hip-hop可能是初中听林肯公园,后来有一次去新华书店,看到几张专辑就给买回去了,有50 Cent的《The Massacre》,听了以后就觉得很酷很喜欢,想知道他们的歌词在唱什么,就去网络上看网友的翻译。看了之后就震惊了,这不就是坏人吗?居然在称颂大坏蛋。后来意识到其实是告诉我英雄不是圣人,英雄跟圣人是不画等号的,这些都带给我震撼。我希望去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可以是很酷的英雄,但也有性格上的瑕疵,这是我想要找的宣泄点,而不在于要去刻画一个什么大时代。
“我尽量避免符号化”
被评价为“说唱贾樟柯”的夏之禹本人有着与大众不一样的看法,“不是我刻意要回避他,而是我觉得夏之禹跟贾樟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在专辑的创作过程中,他还会想办法弱化某个时代的特征。
南都:你有提到过想要做一个“世代发声者”的叛徒,因为觉得发声会背负上一些使命,为何有这种执念?
夏之禹:不背使命这个东西,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不想过于强调是某一个时代,包括里面有很多架空的内容。就比如说《在青少年俱乐部喝醉酒》里“姑娘们听完都说不够要加我Wechat”,那时候没有Wechat这种东西,这种BUG我是回避不掉的,我也没有刻意回。我只希望它抽离感更强。
南都:所以你不喜欢“说唱贾樟柯”这个title?
夏之禹:这个我要吐槽一下,因为经常有媒体要加这个头衔,包括什么“大时代”,我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还原某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我其实还小,所以其实我尽量避免了很多符号化的东西。另外我觉得我跟贾樟柯也不一样,并不是我刻意要回避他,是真的是不一样。
南都:会有人说你是“浪漫派说唱”,你觉得你自己的作品浪漫在什么地方?
夏之禹:就浪漫在特别不现实,以《地主街》为例,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服务行业比较发达的商业中心,很多底层人民生活在那里。我在歌曲里面把他们描写得非常美好,但其实生活在那里的人彼此很冷漠。《Young Fresh Chin》中我只是借用了当时的大环境,并没有很写实,现实情况会冷酷得多。我不希望过于赤裸地把一个东西写到让听众无法呼吸,我想通过自己的手法吸引到别人,而不是用话题去压迫别人。有时候我也想写得现实点,但还是会比较浪漫,所以老板对我的评价就是社会化失败,如果社会化成功了可能就会冰冷点。
南都:社会化失败,这是指什么?
夏之禹:就是没有正经地上过班嘛,不太能社交。很多人觉得我社交能力很强,但其实只是话多而已。
南都:毕业之后就没有正式地上过班?
夏之禹:上过,但也是天意吧。本身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难融入社会的人。我去职场也呆过,但是有些职场氛围让我特别受不了。去上班就会有很多不理解的事情。然后刚好有一点不成器的小才华,老板就愿意一直包容我。
“我喜欢自己瞎琢磨”
说到下一张专辑时,夏之禹提到了“祛魅”,“就是给知识文化或者事物去神秘化,我想尽可能还原每一个东西本真的样子”。本身有很多想法,甚至有些天马行空,但夏之禹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自认通透。
南都:你有引用程璐的“不努力不放弃”来形容自己,生活中就这么chill吗?
夏之禹:没有,就社会化失败嘛。我其实没那么chill,就不是一个很chill很放松的人。我是一个经常挺局促的人,只是为什么显得那么chill呢,程璐老师简直是说到了我心坎里。说白了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类是不太行的,我对人类的未来是不抱希望的,所以我觉得都不抱希望了,那还努什么力啊?那我就躺下好了,不是把一切都好像看得很通透,其实看得一点都不通透,我是很悲观的人。
南都:都说三十而立,你是过了三十岁更悲观吗?
夏之禹:也真的是过了三十岁,突然有一天对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愧疚感。在节目上我说希望各位年轻的创作者养成思考的习惯,而不是写歌的时候才思考。但我的意思并不是大部分人所解读的思考哲学、宇宙、人生,我的意思其实是多去想一想自己不理解的一些很生活化的事。我特别喜欢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其实更准确地说还是自己喜欢瞎琢磨,年轻创作者应该养成瞎琢磨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就跟练乐器一样,你的活儿要一直拿在手上。
南都:所以《Hometown》就是你瞎琢磨出来的?
夏之禹:就是某一天躺在床上就想到宝轮那个镇,当地本来有原住民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突然来了一群外来人要修水坝还是开矿,外来人有高高在上的姿态,筑起高墙,还拉上铁丝网,不让本地人接触生活区,和普通的小镇比起来还挺魔幻的。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不是宝轮人,我觉得有对不起当地人,明明人家在这里好好的,一群外来人还趾高气扬,所以外来人的后代活该挨揍,《Hometown》第二段我稍稍地表达了一点点这个意思。
南都:你之前说过举重若轻是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
夏之禹:可能是我怕尴尬吧,情绪表达太浓烈的东西就容易压迫别人,比如说你几个朋友一起喝酒,然后突然有个朋友开始聊他的前任,聊得声泪俱下,你在旁边尴不尴尬?我就希望不要用压迫式的方式去跟别人聊天,就是好像我聊成这样了,你都还不跟我共情?那你就不是人。希望通过自己的手法吸引到别人来听你说话,而不是用你的话题去压迫别人,或者用你的那种很沉重的句子去压迫别人。
南都:不想要压迫感,用自己的手法吸引人,你自己理解的音乐性是什么样的?
夏之禹:我自己理解的音乐性和弹幕刷的那个音乐性不太一样。有人觉得一首歌的桥段设计得越复杂,就越有音乐性,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哪怕就是在一个很单调的loop里面,你找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律动,即便你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把大家带入到这个律动里,你就是有音乐性的。所以我那天发微博也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觉得音乐性就是一首歌变来变去,好像都分不清副歌在哪儿,主歌在哪儿,这不是我理解的音乐性。
南都:说唱贾樟柯你不认,但浪漫说唱你认吗?接下来会试着换别的音乐风格吗?
夏之禹:浪漫说唱是OK的,这个我是认的。未来时间还长,也不是带着一种突破的心,就去试试嘛。以前我也试过trap,做出来词也OK,flow也OK,但是我这种虚弱的状态唱出来就非常没有说服力。那我就暂时不要做这个,但是都会去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