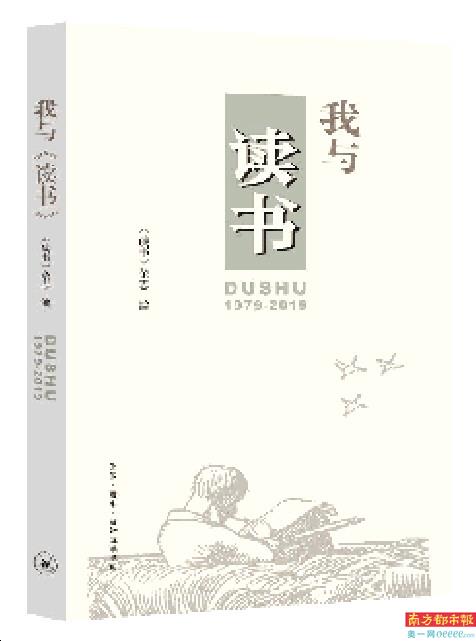
《我与〈读书〉》,《读书》杂志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72.00元。
□ 姚一鸣
2019年是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周年,这本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人文杂志,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它把学术界的声音传递给了广大的受教育阶层,是年轻学子们向往的纸刊平台。年届“不惑”的《读书》,并没有做什么庆典之类,也没有出庆祝专刊,而是在第二年,奉献给读者一本大书,那就是《我与〈读书〉》。
《我与〈读书〉》共分为三辑,一是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回忆文章,二是前辈编者和逝去作者的旧文,三是历任主编和执行主编的回忆文章,是《读书》杂志四十周年最好的回顾,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第二部分,虽然是旧文,但足以证明《读书》杂志一路所经历的风雨,以及对人文精神的坚持。窃以为,如果有一辑“读者眼中的《读书》四十年”,让普通读者谈《读书》对他们的影响,则更完美。
捧读《我与〈读书〉》,不由地引出与《读书》杂志诸多的往事来:
《读书》这样的学术文化杂志,不显山不露水,始终坚持刊发学术文章的标准,几十年以来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识,也是三联书店的名牌杂志。但以阅读的眼光来看,八、九十年代的最具可读性,黄裳、冯亦代、金克木、恺蒂、董桥、施康强、王蒙、董乐山、董鼎山、柯灵等,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些浅显而富有哲理的文章,都十分爱看,当然杂志中还有些涉及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的文章,颇有点深奥,但并不阻碍人们喜欢《读书》,且奉为经典。而其中尤以黄裳的文章最受人喜爱,或谈古书版本,或谈文坛掌故,在《读书》刊文期间,黄裳也焕发了第二春。
1982年2月,黄裳出版了《榆下说书》,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刊于《读书》杂志的,内容也涵盖了古书掌故、历史札记等,很多人认识黄裳的文章,正是从《读书》和这本书开始的。而说到《榆下说书》,还有段淘书的故事。从《读书》杂志上看到出版广告后,曾特地去了次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那时还是闭架售书,可能去晚了,营业员说《榆下说书》已经售缺。以后找遍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均未买到此书,只能从同学处借了一本,读后颇为喜欢。那时就想,什么时候能拥有此书。一直到十多年以后,在福州路上的特价书店旧书处,买到了这本《榆下说书》,也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榆下说书》是三联“读书文丛”中的一本,其他还有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李一氓的《一氓题跋》、陈原的《书林漫步》、杨宪益的《译余偶拾》、杜渐的《书海夜航》等,都是和书有关的内容,陈原、杨宪益、杜渐等的文章也大多在《读书》上发表过,这套小三十二开的丛书,展现出三联书话系列的特点。2009年又出版过《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一2009)》,有六、七册之多,辑选了《读书》三十年来的优秀文章,似感觉不如之前的“读书文丛”精彩。
2011年,曾担任过《读书》杂志编辑的扬之水(赵丽雅),出版了《〈读书〉十年》一书,共分为三册,时间跨度为1986年至1996年,全书用日记体的形式,从作者个人的角度,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的种种情况,书稿以编辑部日常活动、编著往来等为主要内容,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而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和徐梵澄、张中行等先生的交往,从中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能在《读书》这样一本在知识界享有盛誉的杂志中担任编辑,《〈读书〉十年》体现出的是浓浓的书卷之气。巧的是我从犀牛书店所购《读书》的合订本,正是扬之水参与编辑的最后几期(据相关回忆,扬之水是1996年4月15日离任《读书》编辑的),翻到《读书》最后一页,“赵丽雅”大名赫然在列。
最早买到《读书》(1979年4月10日出版)的创刊号,是在四十年前了,记得是在上海长宁区中山公园边上的一个邮局买到这本杂志的,素面朝天的封面上,“读书”二字特别的醒目。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常用家长给的零花钱买些杂志,有《收获》《艺术世界》《大众电影》《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等,那时的邮政局是除书店以外去的第二多的地方,因为有期刊杂志可卖,在书报亭出现以前,期刊杂志大多购于邮局报刊门市部,记得常去的有天山一条街、曹家渡、江苏路、静安寺等处。
现在邮局已不出售报刊,中山公园附近的邮局早不见了踪影,一同消失的还有带有我少年观影记录的长宁电影院,还有愚园路上的中山公园新华书店。在原中山公园邮局的地方,变成了一家餐厅,现在也拆除了。唯独愚园路江苏路口的报刊门市部,一直坚持到了前几年,我还去过几次,记得是买了一本新出的《读书》,和几张报纸,有种重回八十年代读书岁月的感觉,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令人挥之不去的,是有关购书买期刊的记忆,还有沉浸于知识文化海洋中的快乐。其实当初购来《读书》杂志,是有些误解,以为就是本书评杂志,读了以后才觉有些深奧,并不是一个初涉书海的中学生所能理解的,但我还是坚持买了有几年,越读越喜欢,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不再每期都买了,偶尔看到喜欢的文章才会买上一本。前年家里书房装修,我又翻出了《读书》杂志创刊号,如见故人一般,创刊号的纸页已经陈旧,如同我鬓角增添的白发一样,人和书一起变老。
在读书日渐式微、网络阅读渐成气候的当下,一本人文学术类读书杂志,如何有下一个四十年,甚至一百年,是四十以后仍“惑”的。读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许是年过四十以后才渐渐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