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伊维德教授在中山大学参加“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伊维德教授在广州与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成员共餐。前排左起依次为康保成教授、黄天骥教授和伊维德教授。

《甘肃河西<平天仙姑宝卷>及其他宝卷五种》(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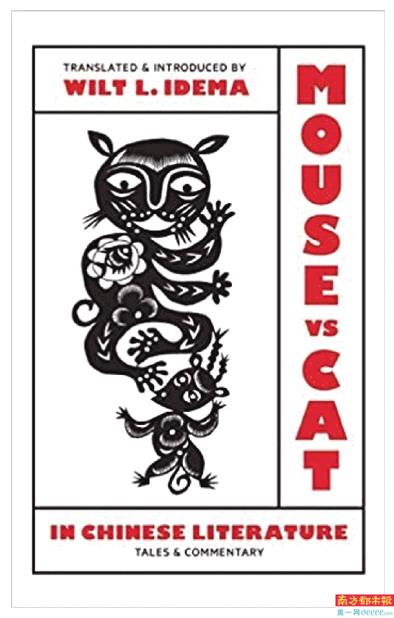
《中国文学中的猫鼠故事与评论》(2019年)

《彤管:中华帝国时期的妇女文学》(2004年)

扫码看专题
自1968年大学毕业后,伊维德在汉学研究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2000年前,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2000年-2013年,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任教,可谓从欧洲汉学和北美汉学两种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伊维德不但学术成果丰硕,而且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被认为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
《大唐狄公案》让他倾心中国文化
伊维德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早让他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是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小说《群芳庭》和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小说《大唐狄公案》。高罗佩是荷兰职业外交官,尽管仕途一帆风顺,但流芳后世的却是他的业余汉学家的成就。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风靡一时。“快读完高中的时候我决心要学习一种语言、钻研一种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不但跟我的母语和文化差异越大越好,而且要有悠久的历史,还得充满活力。就这样我选择了中文。”
伊维德在莱顿大学读书期间迷上了明清白话小说,博士毕业论文就选了早期话本的版本研究作为题目。然而,让他在国际汉学界声誉日隆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却源自他在日本留学时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教授为我和其他一些外国学生组织了元剧阅读课,这使我第一次涉足中国戏曲的研究。”
伊维德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中国古代戏剧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同时,伊维德还参与编撰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等。此外,伊维德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在哈佛大学时一直教授有关中国妇女文学的课程,曾于2004年与管佩达(Beata Grant)教授合编了《彤管:中华帝国时期的妇女文学》,并与方秀洁于2009年合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
钟爱俗文学,尤看重版本
伊维德挚爱中国文化,尤其钟爱中国通俗文学,对中国民间文学和说唱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宽泛,有些说唱文学文献甚至是国人鲜有听闻的,譬如宝卷。他出版了《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的宝卷》。“我对宝卷的兴趣,不在于它是明清新兴宗教或教派的圣典,而在于它对许多民间故事的说唱演绎,包括宗教故事,例如孝子目连的传说、妙善公主的传说。”他幽默地说,“宝卷对译者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在于它们篇幅有限:我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完成《雷峰宝卷》的翻译并找到出版商,而翻译《义妖传》则要花上很多年,而且出版的机会也很小,因为太长了!当然,我希望我对宗教传说类宝卷的翻译也能在讲授中国宗教的课堂上发挥作用。”
治学过程中,伊维德尤其看重版本学的意义。他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这些差异看成‘大同小异’,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着迷于这些‘小异’。当我们把戏剧改编也考虑进来,这些差异就变得更加迷人了。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则是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比较过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剧本。”
专访
“传统”的中国戏曲也一直在变化
南都:您和奚如谷教授合写的《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主要论述了元代戏曲,您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作用和价值?
伊维德:传统中国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社会。“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味稳定,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戏剧亦是如此。你不能先验地假设19世纪的演出条件和13世纪的大致相同。因此,要想知道元曲是怎么演出的,你就得研究元代剧场的情况:我们对男女演员了解多少,对观众了解多少,对演出场地又了解多少。搜集了相关资料,你就会发现元代以及明初跟明后期有很大的不同,而十六十七世纪又跟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仍然认为,对于学习中国早期戏剧的、想了解更多早期演出传统的西方学生来说,《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在准备该书材料时,我们收入了几出与演员相关的戏。这些剧目恰好反映了元杂剧出版的不同阶段。学者们当然一直都清楚,明版元杂剧被大幅改编过,因此不能借助在晚明时期被改编过、充当明代文人读物的元杂剧版本,来研究元代戏曲,把它们当成对元代社会、文化的忠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和奚如谷一直努力把元代和明初不同时期的版本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不止一次将同一个剧本的不同版本翻译出来,就是为了强调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
南都:您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您参与或独自的系列著作中,《西厢记》选择的是最早的明弘治十一年刻本为底本,还翻译出版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十种版本》《化蝶: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四种版本及相关文献》《木兰从军》等等,您是如何想到翻译这些民间传说或剧本的?您似乎对版本特别看重,为什么?
伊维德:中国的传统白话小说是为读者创作的。它可能会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可以自由运用日常的口述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直接取自于专业作者理想化的“台词本”(Promptbooks)。“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白话文学与通俗文学画上了等号,因为他们需要一种中国的通俗文化传统来捍卫自己的文学纲领(literary program),但他们选作“通俗文学”的作品其实属于几百年来文人们就一直热衷阅读、创作的小说和戏剧文类,而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通俗文学。只有少数几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真正对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的鲜活传统感兴趣。然而,当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时,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就已经确立,它没有为多数中国传统韵文和说唱文学留下多少空间,比如宝卷、弹词、鼓词等等——更不用说闽南话和粤语等方言的韵文叙事传统了。而在这些韵文和说唱文学的书面传统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形态,抑或说口头文学!
在受邀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稿时,我很欣慰自己有机会撰写关于说唱文学和韵文叙事的那一章。然而,当我在哈佛大学想给本科生讲这个题目时,由于要提前准备好相关译文,我才发现只有很少的明清说唱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文。因此,我开始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翻译这方面的材料。开始做之后,其文类和主题的多样性、以及对每一个故事的多种处理手法,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是只有一个孟姜女的故事,而是有几十个孟姜女的故事,甚至可能有几百个!其他著名的传说也是如此,比如《白蛇传》或《梁山伯与祝英台》。每种文类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取决于创作的时间和地点,作者的才华、文类的要求以及每种文类的特定受众。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这些差异看成“大同小异”,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着迷于这些“小异”。当我们把戏剧改编也考虑进来,这些差异就变得更加迷人了。戏剧要求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此在许多地方说唱文学作品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并没有以化蝶为结尾,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二人还阳,所以“呆子”梁山伯能变成有男子气概的英雄,而敢于冲破枷锁的祝英台则能表现出她的妇德。
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则是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比较过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剧本)。
注重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女性诗歌
南都:您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颇有关注,除了与管佩达教授合作的《彤管:中国帝制时代的女性文学》外,还与方秀洁共同编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请结合著作谈谈您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看法?
伊维德: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大多是少数精英男人为其他少数精英男人所写的文学,写的也是精英男人的活动。因此,尽管文学作品的规模很大、质量很高,但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反映的都只是极少数中国人的情感和愿望。如果我们对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情感和愿望也感兴趣,那么女性当然应该是首先加以考虑的群体。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文学理论中出现过许多种“主义”,我认为女性主义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一种。假如我更早些移居美国,并且在那里展开我的学术生涯,那么我很可能不敢涉足中国前现代女性文学领域。因为,在北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已经吸引了许多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学者。而在荷兰,研究中国前现代文学的专家其实很少,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用荷兰语写一本关于中国女作家生活的书,配上大量她们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的译文。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讲述了秋瑾这个人物,她的悲剧命运也赋予本书书名:《断头的女性主义者》(De onthoofde feministe)。当我来到哈佛以后,有人建议我把它译成英文出版。因为想让本书覆盖内容更完整,我联系了管佩达教授,因为她是佛教女诗人研究的权威。我们合作的成果就是《彤管》。后来,在美国,我还出版了《满族女性诗歌两百年》,从19位作者的创作中挑选了丰富的作品,并附有每位作者现存传记资料的完整译文。我也被选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选的编者,并且执笔关于英文世界对中国女作家的学术研究概况。但编选工作应首先归功于方秀洁,因为她为麦吉尔-哈佛明清女性写作数据库做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她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开创性作用,也为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我很喜欢研究和翻译女性诗歌。它们很少因为炫学而面目模糊,而许多同时代男性诗人的作品却因之受损。而且她们的部分作品讲出了一些男性作家很少触及的两性生活的侧面。
南都:您目前正在着手进行什么研究项目?近期是否有新的出版计划?
伊维德:对动物故事的兴趣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例如,我因此翻译了一本书,书中收入了对老鼠在阴曹地府里控告猫这一故事的各种改编。另一本书则有关中国文学里的各种昆虫形象。文末一篇是一出短剧,讲的是虱子在阴曹地府里控告跳蚤和臭虫。我跟一位专门研究韩国文学的同事合作,出版了一本《金牛王子》传说的译文集。这个传说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流传到了韩国,中文、韩文的版本都有。最近我则一直在翻译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改变《聊斋志异》故事的、很可能创作于蒲松龄晚年的作品,而是他早期的那些俚曲。我翻译的蒲松龄《快曲》(讲赤壁之战后张飞将逃跑的曹操刺死的故事)今年将在香港《译丛》杂志发表。目前,我在做《增补幸云曲》(讲明武宗朱厚照与一名大同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计划明年问世。
“中国文学研究中所谓‘西方方法’的问题被夸大了”
南都:您的研究领域涉及诗歌、话本、戏曲、小说、说唱文学、女性文学等,在您看来,海外学者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主题、视角、方法论等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您如何看待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
伊维德:在中国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学,跟在外国研究中国文学,本质上就不同。在任何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和教学,或多或少都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中国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既有优势(例如有充足的教学和研究经费)又有劣势(例如政府的关注或干预)。通过学习,学生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这就很难避免对自己国家的作者评价过高、甚至夸大其词的倾向。可是,在中国以外,中国文学只是众多其他文学中的一种,须要去竞争以获得他国读者的注意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就必须在比较的语境中,解释中国文学在哪些方面与其他文学不同,在哪些方面又是相似的。
比方说,在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被认为是作者情感的真诚表达,而在西方,文学首先被视为虚构。再如,启发中国文学的是儒家和佛教哲学,而启发欧洲文学的则是基督教哲学,但这二者往往是冲突的。所有这些鸿沟是可以跨越的,但这需要批评家、译者和读者都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即便这些鸿沟被跨越了,也还存在对许多外国读者来说中文名字过于相似和难以发音的问题。用中文学习中国文学、教中国文学是一回事,在国外学中国文学和教中国文学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所谓“西方方法”的问题,是被夸大了。我们的研究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要向外国观众介绍中国作品却不考虑外国的特定背景,这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从外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很有启发性,让人意识到那些非常有趣却长期以来都被忽视的问题。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把某种方法视为无用而排斥,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布丁是什么味道,就得先尝一尝。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每次我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我都感到很荣幸。所以,当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康保成教授找到我,提议将我之前已经以中文发表过的文章重新结集、收入他主编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出版时,我就更感觉备受荣宠了。
多次来穗在中山大学访问研学
南都:看来您跟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渊源颇深,可以谈谈您跟这一团队成员譬如创立者王季思先生等人的交往吗?
伊维德:任何一位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无论从事哪个题目的研究,首先会做的就是参考中国同行的著作。拜数字技术所赐,这方面是比以前容易多了,只要大学能出钱订阅提供中国出版物访问权限的数据库就行了。没有人能忽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会是中国同行研究的翻版: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在发布研究成果时,我们面对的受众的需求也不同。但优秀的汉学著作一定会对其使用的中国研究成果予以充分的尊重。假如和中国同行研究的是同一批材料,那么我们当然也会想与中国同行见见面,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又是怎么做的。我还清晰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跟中国同行的初次会面,以及首次应邀出席的中国学术会议。我们都衷心希望,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学者们可以再次面对面交流,畅谈共同关注的话题。
我对广州的第一印象可以追溯到1978年、1979年,那时我充当导游短期造访过这座城市。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山大学,在那之前,我去了北京,为北京大学和莱顿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做筹备工作。那时,我已经对《西厢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本希望能借机见到王季思教授。但是,北京大学外事处和中山大学外事处之间的沟通出了点问题。当我在广州下了火车,本以为会有中山大学的人来接我,但没有。等了一阵子无果后,我向警方求助。我在火车站派出所呆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中的一位联系了学校,终于有人来接我了。由于另有活动,王季思教授当时没有见到我,但他把他刚出版的一些书签了名寄给了我。至今,我一直珍藏着这些书。2017年,我去中山大学参加“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时,正值毕业季,所有即将毕业的学生都身着礼服,在拍毕业照(女生们穿着民国服饰),真是一景啊。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策划:王海军
统筹:刘炜茗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翻译:刘铮 审校:陈熙
本期责编: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