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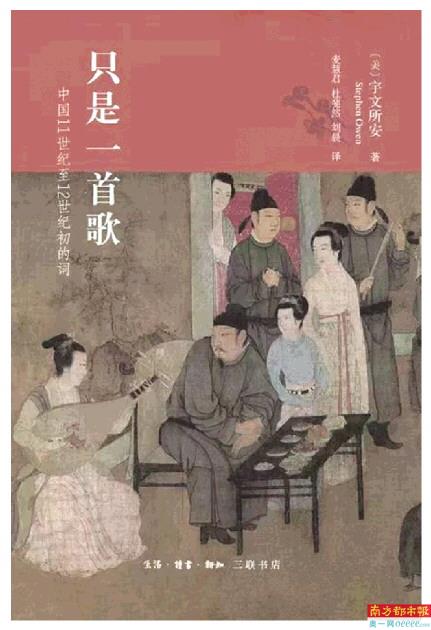

(访谈见报有删减,请扫码在南都APP上阅读访谈全文)
新冠疫情之前,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夫妇几乎每年回一次中国,待上个把月,但新冠疫情让跨国旅行变得困难。宇文所安说:“有许多中国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想念他们”。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巨擘。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他沉湎于诗歌阅读,首次接触到庞德翻译的李白诗歌《长干行》,“遂决定与其发生恋爱”。1972年,宇文所安凭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执教耶鲁大学,后履职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
他的物理学家的父亲曾担忧研究中国诗难以“自立”,四十多年后,宇文所安告诉南都记者:“能以阅读和教授诗歌谋生,此生幸甚。”
备受中国读者追捧的汉学家
博物馆里展出的商周青铜器皿,让宇文所安心驰神往。论及他颇富创见的对唐代诗人的阐释,宇文所安用了一个比喻:他将青铜器皿周身的铜绿比作古典诗歌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某种意义的锈蚀。而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层锈蚀,恢复词语原本的光泽。
31岁,宇文所安以《初唐诗》一举成名。在这本书里,他首次对当时不受学界重视的初唐诗歌进行整体性考察,结合唐诗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透辟地辨析初唐诗歌的特色和美学成就。随后,他又陆续出版《盛唐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迷楼》等著作,以非凡的文献功夫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在唐诗研究的畛域建树卓著。
中国大陆对宇文所安作品的译介在时间上延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2004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首次成体系地译介其学术成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迷楼》《追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等数本。这套作品呈现出如唐诗般清新刚健的气息,新见迭出。它迅速突破了古典文学的学科壁垒,一时间,宇文所安的大名在高校学子乃至普通读者中如雷贯耳,对《追忆》等作品的谈论亦成风尚。
在某读书网站相关条目下,读者们热情地称宇文所安为“美国文青”“一个深深迷恋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人”“可爱的老头”。
2010年,宇文所安与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语世界面世。这部巨著被看作当时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实践,而其采用的“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去经典化”的叙述策略,在中文学界也引起广泛讨论。
宇文所安对文学史有独特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学史绝非“名家”史。他更感兴趣于抉发宏大叙事之外的有关作者和作品的真相。他自称“历史主义者”:述而不作。“我只是拣起那些被遗忘的,不被看见的,或掩埋在尘土里的东西。”此种理念贯穿宇文所安学术生涯的始终,成为理解其诗学思想的密钥。
既实用又有趣的翻译实践
不容忽略的是,宇文所安还是一位勤勉而杰出的译者。他很早就开始大量迻译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论,包括初唐诗、盛唐诗和晚唐诗七百余首,他还翻译了杜甫诗歌的首部英文全集,虽然“细致入微、带有层次感地理解杜甫是十分困难的”,但经由翻译,他发现了杜甫天才的“隐秘的角落”。1152页的《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初始至1911年》,则被宇文所安定义为“作为‘译文’来说最有意思的产品”。
巧的是,早于“宇文所安作品系列”,他的第一部迻译入汉语的作品也是一部译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是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论的教案集结,包括《文心雕龙》等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及评点。
宇文所安有两种翻译实践:一种是实用性的,为了让不通中文的学生凭借译文学习汉语诗歌。在教授这些诗文时,他常不动声色地观察学生脸上的表情,以此判断“哪些文本是成功的,哪些不成功”。
另一种翻译则使用非同寻常的“戏剧化”手段:他仿佛化身为莎士比亚或《桃花扇》的作者,把翻译的中国作家想象成不同的角色,赋予他她们不同的个性及言说方式,以便在译文中传达万千种感性而微妙的诗意的“差别”,并由此突破对英译汉语诗的类型化陈见。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宇文所安说:“而且,从我学生的反应来看,它效果不错。”
“关于宋词我有些话要说”
2018年5月,在执教四十七年之后,宇文所安从哈佛大学荣退。2019年,他研究宋词的新著《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英文版出版,并于2020年斩获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汉学奖”。
在《只是一首歌》的序言里,宇文所安坦言教学相长,写作和研究是孤独的事情,而教学“给学术注入了生命力”。
《只是一首歌》的主体内容便来源于宇文所安过去十多年开设的宋词研讨课。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今年也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宇文所安追踪了词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发展轨迹。他卓有见地地讨论了早期词集的编撰与流通,词作的“重出”现象,词的“感性”话语体系,以及词人形象(譬如李清照)如何被选本及时代趣味所塑造。
这部作品是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由唐转宋”的标志。宇文所安说:“关于宋词我有一些话要说,我希望它能够激发起关于词的新的兴趣。”
当谈及海外学者的贡献,宇文所安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很“多元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群体。“但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外国/海外的学者’。我说的一切不仅仅是一位中国文学学者的意见,而是‘一位外国/海外学者的见解’。这对我来说是有些奇怪和不适的。”宇文所安略为遗憾地说,“我希望不是这样。”
南都专访宇文所安
清除诗歌语言的“锈蚀”
南都:您对唐诗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把诗人和作品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放到一起来做整体评述。这是一个挑战,不单要熟悉文学作品,同时要去考量中国的历史。这个模式有受到某位前辈的启发吗?
宇文所安:这个方法来自我阅读的大量文学史和关于文学史的学术著作,其中包括用汉语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包括欧洲、伊斯兰和南亚的文学史。我经常思考怎样把研究做好,我的想法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我不认为这种研究是为了研究本身而做的,它事实上是构建特定文学文本的阅读框架的诸多可能方式之一。通常,我们经由文学史首次接触到对来自其他历史时期或其他文化的文本的解读,而文学史同样也指出了另一些形态的语境架构的可能。
从我耶鲁大学的老师开始,我可以罗列和讨论一长串曾经启发影响过我的作家、学者。然而,我始终坚信——既践行在我的工作中,也作为我教育学生的原则——对于一位文学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到原始文本并熟知它们。这也适用于对语境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考量在时间上最接近于对象文本的那些书写。
至于说“挑战”,我只能说,能通过阅读和教授诗歌谋生,此生幸甚。
南都:对唐代诗人的形象阐释,您的建构非常有新意,和中国传统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让读者耳目一新。当然,也有评论者认为有些是出于您个人的创造性想象。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宇文所安:无论它们多么奇妙,我们在博物馆岑寂的光线里看到的古老青铜器并不属于那儿。即便现在,它们也自有其独特的美丽,但它们并不是为我们这个世界创造的。它们应该被打磨得金光闪闪,悬挂在熊熊燃烧的火上……这是我的“创造性想象”吗?或者它只是把我们已知的东西汇聚在一起,整合它们,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描述?
诗歌难道不值得被同样对待吗?它的语言也已经生出了锈蚀的铜绿。许多人更愿意接受铜锈斑斑的诗歌,他们在孩童时代就这样学习它们。这当然没有问题,那些将唐代的用法和现代用法简单对等起来的注释也并不是错误的。唐代诗人发展出了一些固定的特征,它们不断被重复,选择那些符合这些标准特征的诗歌是一件让人感到安妥的事。
但是,在阅读诗歌或阅读与诗歌有关的文本时,我不时会瞥见“被打磨得锃亮的青铜的闪光”,我试图清除那层锈蚀。举个例子,大概是在杜甫逝世后十年间,樊晃编了一部杜诗小集,在这部业已散佚的集子的序言里,樊晃给出了关于杜诗接受的最早评论:“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尔,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这显然暗示着江左词人不知道杜甫的伟大之处。我也相信杜甫有“大雅之作”,但我对他的“戏题剧论”深感兴趣,它意味着机智、诙谐与游戏精神。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机智的语言通常很难传世:在语言历史中的某一刻令人觉得好笑的东西,三百年后读来可能毫无风趣可言:而大约在樊晃过世三百年以后,杜诗笺注方始传世,杜甫也被形塑为“诗圣”。如果你仔细检视杜诗的主题与语言,不难发现他的夔州诗是多么好笑。比如说他是第一个在诗里提及乌鸡并描写自制豆瓣酱如何在罐子里晃荡的诗人。
这导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杜甫注意到细碎的日常事物并发现蕴藉在其中的“轻盈”,此种才能是否与他创作“大雅之作”的能力相关?
我是个历史主义者:“述而不作”。我只是拣起那些被遗忘的,不被看见的,或掩埋在尘土里的东西。
南都:打破朝代分野是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显著特色,您在书中也提出了“文化唐朝”的概念,认为其“始于七世纪五十年代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直至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其中包括宋代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这种创新分期的依据是什么?请简单谈谈您的“文化唐朝”。
宇文所安:有一次,在我主持的唐诗研讨课上,我梳理了所有初唐诗人并列出他们每个人的出生地。我把这份名单交给学生,问他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并不是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在太宗朝,诗人几乎全是北方人,来自有限的几个北方地域。那些家乡原本在北方不太知名的地区的诗人们,有许多举家迁到了长安。还有一些原本是南方人士,但随着南方的陷落,他们也在早些时候被带到了长安。
从公元660年起,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土生土长的南方诗人(譬如骆宾王)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的诗人,比如来自四川的陈子昂;他们的写作相当出色。众所周知,武则天曾在全国搜罗人才,并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进入公元八世纪后,我们能看到愈来愈多年轻诗人来自帝国各个畛域,尤其是南方。正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言里指出,许多通过进士考试者终生只拥有一个很卑微的官位,而且通常是在外省。在太宗朝,长安城和朝堂几乎就是我们在诗中所见的全部世界。到了玄宗朝,我们看到来自各地的愈来愈多的诗人描写长安以外的名胜佳迹和自然景致,他们也并不总是表达生活在长安的愿望。当这些诗人在外省时,他们也写诗给同在外省的相知,不见得写给那些身在长安或洛阳的人。
换句话说,在太宗朝和高宗朝初期,长安和洛阳,就像古罗马,俨然是“拥有”一个帝国的双重城邦,而其外的帝国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由许多地方组成的帝国。与双城带一个帝国的情形相反,我们看到一个“拥有”两个都城的帝国。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并非为求新而求新;我只是不想再写一部这样的文学史,在其中文学作品里蕴藏的深刻社会变迁被朝代的历史所遮蔽。
相比于扭曲文化史以使其紧密依附于政治历史,详述文化史上的巨大变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保留了“唐”的称谓是因为这段文化时期和历史王朝有极大的重叠。
“关于宋词我有一些话要说”
南都:您的著作《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最近在大陆出版。这是中国读者读到您写的第一部关于宋词的学术著作。能否讲讲这本书的缘起?这本书与您在大学里开设的宋词讨论课有什么关联?
宇文所安:《只是一首歌》脱胎于我从1970或1980年代起开设、持续了几十年的宋词研讨课。自从1994年以来,英语世界里还没有出版过研究词的专著,唯一的例外是安娜·希尔兹2006年出版的《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这本书回顾了唐朝而非展望宋朝,这在此书的语境里当然是恰当的。但是关于宋词我有一些话要说,我希望它能够激发起对于词的新的兴趣。
南都:传统的词史实际上是词人史。在《只是一首歌》里您提出了另一种角度,即将词史当作词集史来看待,因为词的作者实际上是由传世书籍缔造出来的。研究词集史对宋词的演变发展能得出哪些新的结论?
宇文所安:你问的问题很好。这些正是我试图在书里回答的问题。简单来说,对于早期作品而言,我们最好去阅读词集,因为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这些作品的出处。在某些后来的词人那里,有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贺铸、周邦彦或吴文英的词集。但在大约11世纪末,我们能看到愈来愈多由作者本人精心编撰的词集。
通常,词集呈现出一位作者的形象,而它又反过来吸引那些符合这一形象的词作。在早期的轶事里,柳永为宫廷作词——我们仍然能读到那些词——可逐渐地,他变成了一个蔑视宫廷的反文化英雄。后一个形象胜出,造就了民间的“柳三变”。没人能找到形象背后真实的人,而形象本身也变动不居。
南都:您在书里写道,11世纪,作者是词的属性;而从12世纪开始,词却成了作者的属性。发生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如何推动宋词逐渐取得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正统地位?
宇文所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解释你的其他几个提问。当我说作者身份是一首词的“属性”,这听起来很后现代,也很“外国”。这本书是用英文写就的,它的目标读者群能够接受这样的表述。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常识,而且几乎所有中国读者都明白用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同一个议题。
假设我有一首七绝。假设我在同时开设一门晚唐诗的研讨课和一门明代诗歌的研讨课,分别面向不同的学生,同时我还被邀请去做一场关于当代古典诗的讲座……由同样的字句组成的同一首诗在三个不同的情境里,得到的反馈或有云泥之别。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看到,作者身份和关于作者身份的语境,对于同一首诗而言是不同的“属性”。这接近于庄子“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理解和价值会随着我们对同一事物的描述而改变。
上述情境也会变化:作者身份也可以不仅仅只是一个属性。比如说我读一首苏轼词,作品的风格显而易见是苏轼的——很难搞错。它常常指称我们熟知的苏轼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以及他应对人生经验的方式。作者的名字不会改变我们对词的阅读:它是显而易见的。这首词就此成为我们对苏轼的理解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史希望一切都像苏轼这样,作者和文本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但是我看到某种深刻而缓慢的改变。在改变的两边都有很美的诗,但是它们的美是不一样的。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
南都:您很早就开始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工作,在这方面成果斐然。请谈谈您这么多年从事诗歌翻译的体会。
宇文所安:你忘了提到诺顿出版的长达1152页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初始至1911年》。在我看来,这是我的翻译实践中作为“译文”来说最有意思的产品;其他翻译都是出于写书写论文的需要,或者帮助中文不够的读者理解原文。
首先,我认为翻译工作取决于你为什么以及为了谁去翻译。《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是为通过译文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学生翻译的。那些诗文我教了几十年,我知道哪些文本是成功的,哪些不成功(观察学生脸上的表情)。假如学生对一个文本没有反应,我会修改我的翻译;假如他们还是没有反应,我就给他们读另外一个文本。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实际。
当我思考翻译的时候,我有一个迥异于寻常翻译实践的态度。大多数迻译入英文的汉语诗歌听起来都像“翻译过来的汉语诗”。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读者不会看到“汉语诗”;他们看到的是差别——存在于时代之间、个体作者之间、文体风格之间的各种差别。因此,对我而言,好的翻译应该向另一种语言里的读者传达这些差别。此种翻译的范型,让我想到戏剧:在伟大的戏剧里,角色是彼此殊异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运用语言的方式,有他或她自己的个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或者在《桃花扇》里,皆是如此。文本的愉悦和深度取决于一个由不同声音组成的“家族”。
因此,当我翻译中国作家的时候,我开始“创造角色”,运用我的英语文学知识来暗示那个“家族”里一代和另一代的区别。我用一些简单的形式上的变体来标记文体的区别。我不希望这些区别太过显眼,但它们又必须是一个英语读者可以领会和习惯的东西。比如翻译文言时我使用“英国英语”,白话则使用“美国英语”。
我还可以说很多,但是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而且,从我学生的反应来看,它效果不错。
南都:2006年您开始翻译杜甫诗集,历时八年完成。翻译杜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
宇文所安:最大的挑战在于,细致入微、带有层次感地理解杜甫是十分困难的——他对汉语的运用有许多创新。而最大的报偿在于发现杜甫天才的“隐秘的角落”,这些角落是此前我没有注意到的。
南都:您曾在一个访谈里谈及自己的学术渊源,说自己“来自解构的家族,却是个古怪的解构主义者”,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宇文所安:首先要说明的是,汉语里对“deconstruction”的标准翻译“解构”是很糟糕的,它导致了许多误解。一种方法是把它看做中国人所熟悉的某种“逆向操作”。你拆开某个东西,以便理解它是如何制造的,它为何被如此制造,以及制造它的方法。语言内部的“逆向操作”是复杂的,因为语言自身就是构成言说的力量。但你的意图不是要摧毁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解构”并非一个“体系”或某种“技术”:在人文学科里,它是调动一切语言资源来理解你所阅读的文本的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举许多例子,但那会占据太多篇幅。
当你将解构作为一种习惯内化在阅读行为当中,你能注意到在其他情况下注意不到的事物。对这些事物,我们可以用文献证明并展示给读者。我在“解构”的家族中是个异类,因为我是个历史主义者。我关注的不是政治史,而是某些新的东西如何以及为什么出现在某一历史时期,文本如何在时代和时代用语的上下文里安置自身。词语的意义和细致含蓄的内涵会改变。此前从未或罕有出现在诗歌中的语词突然频繁地涌现。于是,我们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或者此前一千年里都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些问题让陈旧的文本获得新生。
海外中国文学学者群体是很“多元的”
南都:从哈佛大学荣休之后,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未来是否有新的出版计划?
宇文所安:当我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我自认为在学业上很用功,但仍然有许多时间用来阅读、游戏、思考,并将所思所想付诸笔端。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我开始教书以后,慢慢地我就发觉自己用于做这些事情的时间愈来愈少,总是在完成课题项目或履行职责。我曾期待退休能让我再次获得思考、游戏、阅读的闲暇。我刚刚写完了一部论述楚辞的书里由我主笔的章节,正等待着我的合作者们完成剩余的部分。我还在从事另一些工作,但我不想在当下谈论它们。我退休后的“目标”是阅读、研究和写作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乐趣和享受。我现在还在朝着那个目标努力。
南都:不知您与中国的古典文学学者是否有密切的交流?在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哪些优势?
宇文所安:有许多中国学者都是我的好友。新冠疫情让回到中国变得困难,我很想念他们。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和田晓菲教授每年都会去中国待上个把月左右。
我想谈谈海外的中国文学学者群体:这个群体是很多元的。有像田晓菲教授那样地道的中国人,她依然是中国公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阅读诗歌和文言文;有许多美籍华人,其中一些人年纪很小就来到美国,另一些则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像我一样的美国白人;也有欧洲人。像田教授这样的人感觉很中国化,也非常骄傲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欧洲人则为他们的欧洲传统感到自豪。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些差异:每个学者都只是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学者。没有所谓的“外国学者”或者(在海外的)“本土学者”的特权。这种情况非常珍贵: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很“自在”。但是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外国/海外学者”。我说的一切不仅仅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意见,而是“一位外国/海外学者的见解”。这对我来说是有些奇怪和不适的。我希望不是这样。
南都:您和田晓菲教授是著名的学术伉俪。在学术研究方面,你们二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宇文所安:我不会将它称作“影响”,但我们喜欢的许多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在一起开怀大笑,我们分享彼此的写作,我们也从彼此身上学习。
南都:作为一名汉学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您对中国文学(包括古典的和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如何?
宇文所安:在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之一;而当代中国文学也已成为伟大的民族文学之一。
总策划:戎明昌
策划:王海军
统筹:刘炜茗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刘炜茗 周佩文
翻译:黄茜
审校:田晓菲
本期责编: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