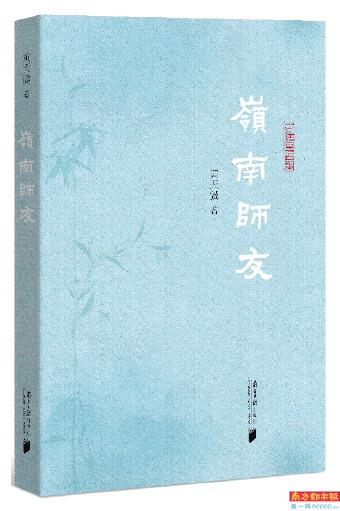
《岭南师友》,黄天骥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张诗洋
黄天骥老师新作《岭南师友》近期出版,嘱我写序,我心里诚惶诚恐。见我迟迟未动,有师兄建议,不妨写写学生们眼中的黄老师。转念一想,自二〇〇九年跟随黄老师求学,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借文章梳理一番恩师教义,自是理所应当的。再者,黄老师找学生写序素有传统。《黄天骥文集》所收皇皇十五卷大著,除了黄修己、金钦俊等先生赠序,其余多是学生辈撰写序言,是老师绛帐传薪、提携后辈的写照。老师既有此美意,我这初生牛犊,但写无妨!
黄天骥老师一九五二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随后留校任教,在中大度过了将近七十年的时光。老师对曾经教过他的师长念念不忘,他说:“好的老师,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他们未必耳提面命,但老师们的道德文章,治学方法,会给人许多启发。”黄老师一遍遍体味着夫子们的春风化雨,体悟耳濡目染中得到的智慧与情怀。老师年幼痛失双亲,把师长当作父亲一样去爱护。回忆起王季思、董每戡等先生的往事,他常常眼眶发红,无语凝噎。他不仅料理了诸位先生的生前身后事,还守先待后、赓续薪火,培养了一支戏曲研究队伍。
黄老师治曲,深受董每戡、王季思二位先生的影响。王先生注重戏曲文本考证与校勘,董先生关注戏曲舞台和演出形态,两位学者双峰并峙,各领风骚(见本书《杏花零落香——记董每戡老师》《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老师》两文)。这“一文一武”的研究范式和治学主张,奠定了黄老师和整个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学术根基。同时,他又得詹安泰、黄海章先生亲传旧体诗词创作技法(见本书《岭南词宗树蕙滋兰——记詹安泰老师》《人淡如菊——记黄海章老师》两文),在诗词、碑文和散文创作方面亦颇有成就。黄老师将师长所教的“戏曲”与“诗文”两种研究路径融会贯通——用诗文创作的思维研究戏曲,又用戏曲的眼光解读诗词。守成之外,敢于创新,成就了黄老师“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的治学面貌。
黄老师对文学的感悟力和审美力,还源自他深厚的艺术修养。老师年轻时原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因为他不仅会演奏曼陀林,而且在合唱指挥上也颇有造诣。后来他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还经常在重大节庆晚会上指挥合唱。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中大指挥合唱队演出,曾得到卡拉扬大师的首肯!余生也晚,未能见到卡拉扬赞誉黄老师的场面,但从师长们的转述中,从近些年亲眼见到老师指挥合唱的盛况中,仍能感受到他气势恢宏的指挥风采。在指导学生时,“黄指挥”的妙法也能派上用场:学生茫然不前时,老师的指挥棒轻轻荡开,嘱其舒缓顺其自然;学生狂飙突进时,老师又大手一挥,引导他们紧跟拍点靠谱演唱。
黄老师一向主张文艺不是中文系师生的课余活动,而是必修课。因着共同的音乐爱好,老师在专业课和文艺爱好方面,都对我鼓励颇多。记得我写博士论文时,有一次文思涩滞于某章,干脆跑去中文堂楼下多功能厅练琴。当时弹的是肖邦的《夜曲》,心情郁闷,琴声也跟着气若游丝。黄老师恰好经过,听了一会儿推门而入,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儿”。《夜曲》的静谧并非单纯用弱音表现,尤其是肖邦这样情思较多者。诗中常讲“月出惊山鸟”“鸟鸣山更幽”,有对比才更具表现力。老师还特别关注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他对《送别》《梁祝》《杜鹃花》等曲目的解读,可谓独具只眼。对音乐的精通,对韵律的敏感,为老师的诗词和戏曲研究增加了另一个触角。
寿过耄耋,黄老师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质优量丰地产出一系列成果。最近这两年,他保持着每个月两篇文章的写作节奏,一篇是唐诗鉴析,一篇是散文创作。散文创作是老师的写作调剂,正题还在于挑战自己,向文学史上“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定论发难。他告诉我,从“人”出发,抓住“人性”这个主题,破除成见,文学史是要改写的。这其中的分量和气魄不言自明。遗憾的是,诗歌的确非我所长。许多文字,我虽幸运地成为第一读者,却没有能力生发开来,与老师展开更有见地的讨论。不过,如何找到小作家的大问题、大作家的新问题,如何处理文献取精用弘,给了我诸多启示。
黄老师一辈子对学术一往情深。《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出版之后,《〈长生殿〉创作论》已列入下一步写作计划中。源源不断的大著,是黄老师毕生的心血,也是学界之大幸。他的学术成就早有公论,为人师表有口皆碑,但老师对名利得失看得很淡。他一生经历过大小劫难,归来仍是一介书生。对别人敬称“大师”等美誉,他一概否定,讪笑只有和尚或风水先生,才被称为“大师”。老师说自己受时代和水平的局限,“顶多只能作为过渡性的桥梁”,学术成就“就那么回事儿”,还总用广式“煲冬瓜”(粤语,谐音“普通话”)刻意拖长结尾的儿化音,以示自我调侃。
其实不仅是身外物“就那么回事儿”,老师甚至对生命本身,都抱持一种顺其自然的畅达思想。一方面,他懂得王季思先生教诲的“学术不靠拼命,靠命长”,因此在研究上很少突击作战,大都从长计议,规律写作。在《全明戏曲》大项目忙得不可开交时,老师上午全心处理明传奇剧本校对稿,中午稍作休息,下午撰写《〈牡丹亭〉创作论》专著,晚饭后总找学生一起,散步聊天,作为放松。早上还要游泳八百到一千米,这比年轻人还要自觉、高效。另一方面,他看淡生死,面对疾病衰老,都秉持一种近乎道家的思想,无为无畏,丰赡舒展。更难得的是,他保留着“老顽童”心态,看电影喜欢武打场面,看球赛只看女排,不看男足。遇到台阶,他一个箭步跨上,走起路来步履飞扬。前几年,有次自行车被盗后,老师竟想换成无扶手的双轮电动平衡车,还说看到别人像踩风火轮一样穿梭,很是帅气。后来他果真去买,不过商家一问他的年纪,不敢卖给他……
黄老师率真,讨厌矫揉造作与刻意修饰。文章如此,做人亦然,结交了不少好友。“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正是因为与真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老师总能从与他们相处的小事中,随手拈出几笔便颇见精神,刻画出诸先生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些感怀友人的文章背后,实在是有所寄托的。如其所写的《一日心期千劫在——记罗宗强教授》一文,还有个小插曲:老师完稿后交与编辑,嘱咐其他文字都可以删改,唯有文中“两件事”不可改动。这篇文章,除了追忆挚友罗教授,还提到了当下学界在意的“博导”身份、刊物定级等问题。黄老师借回忆当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时的工作情况,“让诸君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走了样的现状,皮里春秋,发人深省。明眼人即刻明白老师的深意,这便与一般回忆文章又有所不同了。
黄老师不仅对朋友真诚,对于后进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他尤其能体恤年轻人的不易,愿意为他们说话。他办公室的大门总敞开着,随时欢迎老师同学们去交流。前几年台湾花莲大地震时,他担心台湾学生芳羽的安全,多方联系。直到确认其无恙,老师才放下心来,又一一告知联系人,让他们也安心。得知一位研究生患病,他去找学校附属六院的大夫,嘱咐大夫务必用心诊治,又提醒我们从旁鼓励帮助。学生遇到不顺心的事,他比学生还着急,把眼镜往额头上一推,眯着眼睛,一字一顿地在手机上敲出大段暖心的安慰发给学生。诸位先生传道授业对于黄老师的影响,又何尝不是他后来培育与感化学生辈的源泉呢?
老师一辈子得师长喜欢、受晚辈爱戴。他不爱端架子树权威,既拎得清自己,也看得清他人。他洞明世事,仍富于善意和美感去观照这世界,有血有肉地记录对生活、对师友的热爱。集中所收诸篇,风格各异,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岭南师友”,更可以读到黄老师这个人。对读者来说,喜读故事的,可以从本书中看到历史现场的绝望和希望;欣赏文笔的,可以看到学者型作家遣词造句的老练与鲜活,不期然在书中撞见人生,透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不揣谫陋,漫谈一番如上。个中精妙,留待读者品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张诗洋,文学博士,广州大学副教授。本文为黄天骥著《岭南师友》序,大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