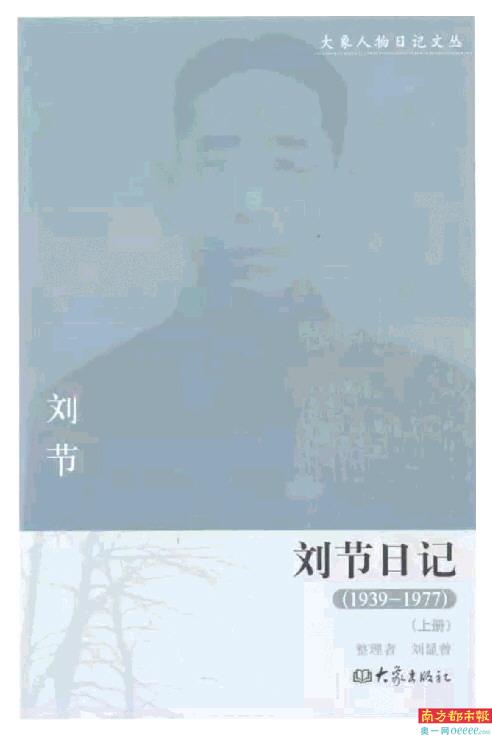
《刘节日记(1939-1977)》,刘节著,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版,98.00元。
□ 贺越明
葛剑雄先生的大作《谭其骧1970年代外事活动日记解读》(载上海《世纪》双月刊2020年第6期),详尽地整理了这位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1970年代涉及接待、出访及通信等外事活动的文字记载。虽是日记体裁,简单扼要,但读来如临其境,颇有兴味。惟读至1972年“5月13日”一条,不免引发笔者的疑惑及思索。
该日所记为:“八点半到物理楼,九点意大利外宾到。乃东方出版社马利亚,女,五十余岁,及其助手菲利普,三十余岁。曾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三年。接待者刘节、徐玉麟、刘大杰、樊树志及国际政治系教师、外文系教师、外文系女学员二人。参观电子工厂及外文系法语班,上课后座谈。饭后继续,至三点半结束。主要问招生办法、教学计划、理论联系实际等。余谈史学界解放后斗争,及唐代文化繁荣昌盛由于北朝末及隋朝末农民起义促使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衰退,代之以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反映到文化之结果及中外交流之结果。”文末有关于这则日记的注释,对日记主人向外宾所述的史观解释“这是当时通行的观点”,而于所列的参与接待者则无说明。
参与接待者中,名列首位的是刘节。从记述的学术交流内容看,当指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古史专家刘节先生。他曾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正直重道的铮铮风骨。可以说,参加外事活动是名誉和地位恢复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待遇。倘使刘节先生去上海参与接待外宾,那便说明其境遇至少从那时起已有改善。
然而,据《刘节日记(1939-1977)》1972年5月“十三日 星期六 天晴”条下所记:“晒书。晚颂曾、穗孙均回家。”(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749页)。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尽显这位学者居家闲置、乏善可陈的寂寥之状。更重要的是,这证实当天他人在广州,绝无可能分身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
莫非谭其骧先生在日记里误记?这种可能性近乎不存在。二位学者同在史学领域,昔年两度同事:1932年,谭其骧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刘节时任该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主任;1936年,谭其骧在燕京大学任讲师,刘节则为同校副教授。他们相交相知,份属好友,互以对方的字“子植”、“季龙”尊称,自然不会错认误记。
1972年刘节不可能到沪参加外事活动,还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佐证:1977年3月20日,谭其骧出差到广州,次日用下榻的广东迎宾馆便笺写信给“子植尊兄”,表示希望与老友晤面。该函开首便说:“不见已二十年,渴念何似!”继而说:“昨因事来穗,寓迎宾馆三号楼三二一室。亟欲趋晤一谈,但不知尊寓地址,何时趋访比较合适?如何坐车?至希函知或用电话通知,拨32950,再叫321室。即颂近祺。”从1977年回溯,“不见已二十年”,他们必定不曾在其间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过相见之缘。23日,刘节的日记有载:“接显曾信、谭季龙信。即复之。”27日下午,谭其骧来到中山大学西南区74号一楼刘节家里。当天刘节日记有载:“下午谭季龙来访谈。”(洪光华:《新发现的一通谭其骧致刘节函》,载2017年5月11日广州《南方都市报》)
其实,对于谭、刘时隔二十年的这次晤面,葛剑雄先生所撰先师谭其骧传记亦有描述:“1977年3月27日,谭其骧去中山大学看望已身患绝症的刘节,当时他因喉癌影响已不能说话,只能以笔交流。他们从下午三时‘谈’至四时三刻,这是他们劫后第一次的会见,也是他们间的最后一次会面。”(《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确实,会面后不久,刘节于当年7月21日病逝。传记将此次确定为“他们劫后第一次的会见”,是因为在发现上述那通谭其骧致刘节函之前已完成并出版,尚不知有一通与此有关的谭其骧手札存世,且言明与刘节“不见已二十年”。即便如此,“劫后第一次”与谭其骧日记里出现刘节之名的1972年5月13日,同样在时间上有明显的抵牾之处。
那么,是否有另一位姓名相同者呢?笔者就此向高龄的朱永嘉先生求教。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人,他回想后肯定地说,上海文史学术界以及复旦大学,包括当时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都没有名叫刘节的人。而且,刘节是治古代史的著名学者,倘若当年到上海,他定会知道并有印象。
谭其骧是历史地理学泰斗,日记颇有文史价值,应作系统整理后完整付梓。葛剑雄先生的大作引言部分说明:“本文据日记原件抄录,删去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但是,“据日记原件抄录”却出现刘节之名,似有违史实。这一奇特之谜,又该如何揭而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