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马伯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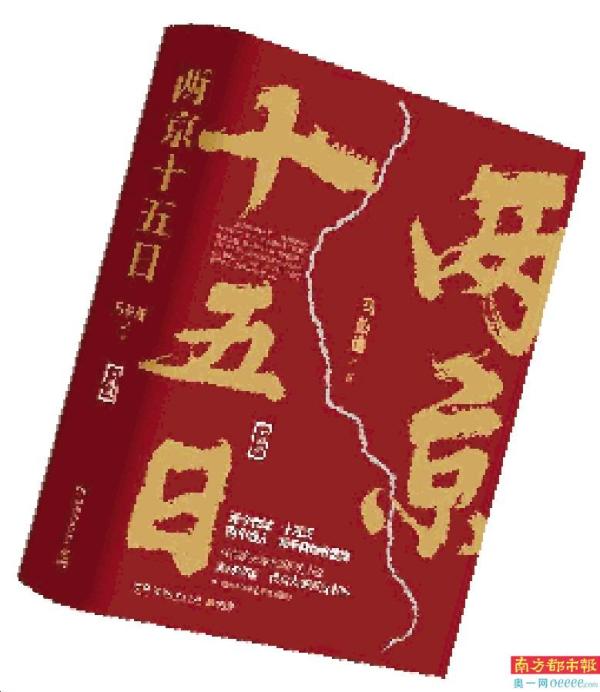

扫码看访谈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邱晓琳 去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紧凑的剧情、讲究的服化道圈粉无数,今年,原著作者马伯庸又写了一部“明朝公路片”,讲述太子跨越南京北京的一段极速之旅,书名《两京十五日》。
和《长安十二时辰》相似,这是又一部马伯庸从“历史的犄角旮旯”里发现并挖掘出来的作品——
“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明史》里的寥寥几句关于明太子朱瞻基的记载,引起了马伯庸的无限遐想。
天子病危消息传来,千里长河,星夜奔驰,太子沿着大运河极速奔跑回京,“我们知道这位太子只用了15天从南京回到了北京,但是这15天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史书上的这段留白,成为了马伯庸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
中国人讲历史故事,大都喜欢帝王将相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中国人了解历史,也往往从二十四史的纪传体,到英雄人物的传奇话本,皆以此为纲。但是,马伯庸想要的方式,是从史料的“犄角旮旯”里翻出细枝末节,循着故事的吉光片羽,探索更别样的历史风景。
《两京十五日》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些历史上具体执行琐碎事务的人。“当过上班族的都懂,领导一句话,下面跑断腿,汉武帝一挥手,几十万汉军出塞去打匈奴,咱们都觉得荡气回肠,但如果你是当时负责粮草的一个小官吏,你要考虑到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后勤补给?你想想这个事儿有多难?”
今年七月,马伯庸还写了中篇小说《长安的荔枝》,讲的是杨贵妃想吃荔枝了,唐玄宗说:“弄点新鲜荔枝给贵妃吃”,就这么一句话,下面的人开始规划,怎样从南方把荔枝一口气运到长安,而且要保证荔枝够新鲜。
有一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马伯庸还有一句话叫“一事功成万头秃”。他在《长安的荔枝》里写了这么一个倒霉小官,“在所有人都认为项目做不下去的时候,任务落到他头上,一咬牙就各种想办法,利用各种方式提高速度,规划路线,找冰块,要到各种资源,把运荔枝这事儿办成了。”
不同于《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固定场景,《两京十五日》里明太子需要从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返回北京,因此书中描绘了京杭大运河一路的沿途风光和风土人情。马伯庸称它为一部“明代的公路片”,不迎合市场,创作“超出读者经验之外”的作品。
在马伯庸看来,写作更像是一个读者和作家双向选择的过程,而作家需要的,是写自己擅长的领域,给读者带来不一样、有启发性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去迎合读者。因为读者读的是一种超出他经验之外的事物。如果我去迎合,实际上迎合的是读者自己经验之内的事物。”马伯庸谈到写作时这样说。
作为一个作品涉及科幻、奇幻、历史、灵异、推理、动漫等题材,创作领域广泛的作家,他对深究历史细节很感兴趣,并以此为乐。
“我希望能尽己所能地把这本书里的细节历史考证得足够精深,达到让有历史知识背景的专业读者觉得这本书看着好像言之有理,是很专业的。喜欢历史的读者会过来看看,不喜欢的慢慢就不看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市场上筛选一些跟我志同道合的读者,聚拢起来。”
近日,马伯庸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很多人看到马伯庸的名字,第一就会想到《离骚》里的“朕皇考曰伯庸”,但其实这个笔名和屈原关系并不大。“我觉得伯庸这两个字中正平和,很符合我的气质。后来没想到,历史上还真的有一个诗人叫马伯庸。”
马伯庸有过很多笔名,最没有名气,也是最令人讶异的一个是“花褪残红青杏小”。
“看名字以为是一个风流俊秀的年轻人,看到我本人也许会失望,但是’伯庸’这个名字,大家会以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看到我本人会吓一跳:原来这么年轻!我想特意让读者产生这种落差。”(笑)
访谈
写出大历史抉择背后的“合力”
南都:你根据《明史》里几十个字的记载,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字,创作过程中,相对于《长安十二时辰》而言,你觉得哪一本的写作难度大?
马伯庸:这本书的难度更大,因为它涉及到京杭大运河沿岸的两千多里地,《长安十二时辰》只是长安这一座城,《两京十五日》写到了从南京到北京,沿途大概十几个大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风貌不一样,大运河的走向趋势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主角是在不断移动中完成这些情节上的功能,这个设计起来比《长安十二时辰》难多了,而且还要符合历史事实。
南都:相比你之前的几部作品,《两京十五日》在叙事技巧上是不是更讲究了?你自己觉得这一次有了哪些进步?
马伯庸:如果说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本书里我除了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之外,还试图放一些思考在里面。比如这本书的主要背景是京杭大运河,而且又面临着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朱棣面临着要不要迁都、大运河是把它废掉,还是继续把它保留住,这样的抉择。这个争论就会衍生出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民生、对军事各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足以写一篇论文的,只是论文很少有人去读,如果我把它放到一个小说故事里去,可能会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南都:《明史》里太子回京这一个小细节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马伯庸:朱瞻基在南京突然接到通知,他爸得病死了,他一路跑回去跑了15天到北京,但是史书没有写他具体是怎么到的。
我这两年开始跑步了,对速度特别敏感。我算了一下,15天从南京到北京,发现怎么算都不对,15天不可能跑到北京。你可能会想到骑马,但是马不是我们想象中可以一天一夜地跑,实际上古代的马持续全力奔驰不可能超过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后马必须要歇着,不歇这马会死。就算马可以累死一批换一批,但人不能换,从南京到北京直线距离两千两百多里,再加上路上弯弯绕绕,可能两千五百多里,太子不可能24小时在马上。骑过马的人都知道,骑马是不能坐着的,骑马是双腿夹住马肚子,屁股虚抬,整个人向前倾,要是长期坐在马鞍子上,你屁股很快会裂开很痛苦。所以综上,太子不可能骑马用15天从南京到北京。
后来我算了一下,发现坐船可以。因为南京到北京正好有京杭大运河。船可以24小时持续不断地走,而且水面基本平稳,不像骑马还要过沟过坎儿,人坐在船上很舒服,没有颠簸之苦,我推测宣德很有可能大部分时间沿着京杭大运河坐船去的,到了天津才改成骑马,一路狂奔到北京,这样才能勉强在15天赶到。我觉得特别好玩,心想要不就写本小说吧。
南都:《明史》里只有寥寥数十字的记载,完成一个长篇需要更扎实的历史知识的储备,你还有参考其他一些比较靠谱的资料吗?
马伯庸:实际上关于这位皇上的遭遇的资料很少,就几十个字。但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文献还是挺多的,尤其是现在国家也在推广大运河文化,相关的一些学术论著、学术论文有很多,我做的工作就是把这种枯燥的学术论文做一个转化,做一个截取,截取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南都:大运河实际上也是一个最近的热门话题,写作期间有没有去田野调查过?
马伯庸:大运河沿线我也是走了一圈,当然没有走全,一些点有专门去考察过,包括他们的一些遗址,沿途河流走向什么都亲自去看过。
南都:你似乎很乐意去截取历史当中的一个微观局部,一段很短的时间,一个很小的人物,去铺陈一个长篇故事,甚至符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这种书写历史视角有什么特别之处?
马伯庸:我特别喜欢这种以小见大,因为如果讲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讲一个大的历史规律,它的视角太高,往往会流于特别空泛的口号。从一个小人物写起,从一个小事儿写起,慢慢地引导读者进入到一个大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大的时代,这种方法比较亲民吧。
每一个大时代,大潮流,大趋势,实际上都是由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组成。我们有时候会说,某一个英明的皇帝、将军、智者,能够突破时代限制走出去,但实际上他的突破也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他们的需求构成的一个合力,我就是想把这种想法在这本书里表现出来。
迁都我们都知道是朱棣一语而定。那么到底他这个决定背后有没有别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他所谓的顺应时代潮流,实际上就是顺应这些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需要呢?而且一两个小人物对时代的影响可能是无足轻重,对这个时代是没有影响。但是当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潮流。我想把这种从末端,一两个小人物到影响到整个朝堂整个朝代大趋势之间的变化写出来,告诉大家说,京杭大运河、从南京迁都北京,这些对中国历史来说的大事儿,背后千千万万人构成的合力。
真正的“悬疑”,是人物的成长
南都:《两京十五日》写的是太子朱瞻基横跨两京飞奔,而在和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司乘李必也是从第一集跑到最后一集,你是否有意将“奔跑”作为串联情节的主线?
马伯庸:我想如果能把动态表现出来的话,也算是一个新的方向,也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感觉。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不光是在朝堂之上,后宫之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很多故事是值得用动态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的。
南都:你会不会在写作《两京十五日》的时候去考虑影视改编的趋势,强调它的故事性?情节设计里是否有对影视语言,尤其是好莱坞电影语言的借鉴?
马伯庸:这个还真没有,因为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影视改编和影视剧的表达是一种视觉的表达,它跟文字的表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你不可能写成一个小说,既让小说好看,然后又可以直接当剧本用,这个难度非常大。很多人可能他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会以为反正都是文字嘛,小说写完了,改成剧本是不是特别容易,或者我看小说的时候觉得画面很好,直接可以拿去当剧本来用,这都是一个误解。
而且这本书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它讲京杭大运河,从南京到北京,一路是沿着河走。那么在影视剧的拍摄,包括火戏、打戏在内,水戏是所有戏里最难拍摄的。如果我是存心要去做影视剧开发的话,那我就直接不走水路了,我直接走陆路的话,可能还好拍一点。
南都:可能当代读者对叙事节奏的需求是越来越快了,尤其在英美剧对年青一代影响这么大的情况下,你在创作小说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脑海中已经先有了影视的一个画面?
马伯庸:倒不会说是脑子里会有影视的画面,肯定还是从文字入手,但是在写的时候,我确实会有一些意识,比如说我会有一个镜头在里面,我会用文字把这个镜头的运镜,把它表现出来,它一个视角的拉远,一个视角突然拉近,一个特写,或者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变化,就是会用文字把这种镜头感写出来,我会假设有一个观众的视觉,观众的视觉是跟着一个虚构的摄像头走的,那么虚构摄像头在我的文字里我会强调他所看到的画面,而且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个画面移动。比如说我写一段城墙,不会直接写“一个高耸入云的城墙”或者“一个巍峨的城墙”,如果你有镜头感的话,你知道一个人肯定是先从上到下看,或者从下到上看,比如说你会先注意到城墙根部的垒垒的青石,然后再慢慢抬起头看上去,看到墙壁凹凸不平的城墙上面挂着青苔,还有一些射箭或者投射击留下的战争的痕迹,抬头会看到黑色的城墙上方是一片战争的天空……很简单的,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它这种描写是一种镜头的描写。
南都:《长安十二时辰》里关于唐代的细节描写令人印象深刻,你的小说也被称为一种“文字考古”,你如何去复原那个时代的衣食住行风俗的日常细节,然后把它很好地融入到小说的故事叙事里,兼顾历史的真实和小说创作的虚构性?
马伯庸:一方面是案头工作,你要考虑得足够细致,当时的人怎么花钱,怎么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坐马车坐什么样的马车,关于这些的资料很多,就看你有没有心思去挖掘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让这些器物本身和情节发生关系,并不是单纯地一个描写,它一定是对情节有所影响,有所推动作用的。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两点,读者读到小说就会感受到,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风貌。
我觉得首先就是那八个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们写大事的时候不能虚构,我写这个难度很大在于,一开始我写到太子遇难,太子碰到危险,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他登基当皇上了,这个历史我改不了,首先这个悬念就不见了,那到底我该怎样在大家知道剧情结尾的情况下,还让大家愿意看下去,也是难度挺大的。
从细节来说,“小事不拘’,不用特别拘束,可以去做适当的发挥。但这种想象,一定是基于当时合理的历史逻辑,我写明代,他们当时人的社会风貌,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用的衣食住行的器物,一定要比较符合史实。比如说我写主角拿个手机,这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东西,当时手写一封信,这是符合事实,但是历史上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他没写过这一封信,不过从技术上可以做到,所以说这种小细节上就可以做一下适当的发挥。因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形态都不一样,比如明代的时候,女性其实不能出来随便走,那我在写女主角的时候,我们必须给她讲一个理由,只有一种女人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就是医生,所以这个女性人物的出现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的。
南都:那怎么让读者知道历史结局的情况下,让读者愿意读下去,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马伯庸:可以设置一些小的悬疑,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物,要让读者喜欢上这个人物,关心人物的命运,而且这个命运不是指他在物理上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朱瞻基最后会当上皇帝,但是朱瞻基这个人,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的出场好像是一个比较顽劣的纨绔太子,后面他会经历什么转变,他最后会领悟到哪些东西,这些读者不知道,所以说真正的悬疑就是人物的成长,当你把人物的成长设置得足够好的时候,读者就会一直关心他,一直读下去。你看《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后来死了,但是我们读到“三顾茅庐”的时候依然很开心,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它的过程,除非你写的一个悬疑感特别强的推理小说,你就靠着最后“谁死了”“谁是凶手”这样的梗来支撑。
从苏轼那儿学习“八面受敌”读书法
南都:你曾经说,为了修订旧作,你会特别去纠一些历史细节是不是真的有考证,比方说地瓜什么时候才从别的朝代引进到中国,“大人”这样的称谓是什么年代才出现等等。
马伯庸:当然有很多学历史非常专业的朋友会跟他们请教,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在学习,自己去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自己经常会看论文和原始资料,推论出很多的细节它到底对不对,我会请专业人士来做一个评判。
我需要把书里的历史细节考证得足够精深,达到让一些专业读者能够觉得这本书言之成理,让普通读者也读进去。比如我书里面写到的南京城墙,“高六丈五尺”,人跳下去肯定得摔死。微博上有一个做古建筑研究的读者给我留言说,他去查了考古报告,发现南京城墙的确就是高六丈五尺,正好三十多米高。我说我的确就是看过考古报告才写进去的。这个细节加不加对情节没影响,但是加上去了,专业读者会认可我的努力,普通读者读完以后也会觉得这个小说虚构的世界可信,只有这样,我才能把他们拽到我的故事里来,听我开始“胡说八道”。
南都:那你内心定位的读者是专业读者,还是不那么熟悉历史的普通读者?你认为写作者的内心应该考虑读者吗?
马伯庸:我每次写小说都会写两遍,第一遍就撒开了写,不会考虑任何市场需求,把我的知识抖出来就够了,写完爽完了,第二遍开始删,一边哭一边删,把影响阅读流畅度,和情节没什么关系的内容,删到读者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写小说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你自己觉得爽,这样你才能保证持续的创作热情,第一遍不能给自己设限,如果你第一遍写就开始担心读者哪里看不懂,担心读者不能接受,那这本书肯定不好看,一定要作者自己爽完之后,再删减,就算删完留下的东西,也比一开始就迎合读者写出来的东西要好。
而且我一直觉得写书没办法去迎合读者,因为读者想读的是没见过的世界,没经历过的风景,读的是超出他经验之外的事物,如果我去迎合读者,我迎合的是读者经验之内的东西,比如什么言情啦狗血啦,都是读者经验之内的,我写了之后带不来惊喜。我写书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等于是在筛选一批和自己志同道合的读者,跟我一起,聚到我这儿来。
南都:你是怎么样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去选择素材的?
马伯庸:其实是靠苏轼教我们的一个读书方法,“八面受敌”读书法,名字听起来很酷,我举例解释一下,比如你是一个学生,碰到一个江湖混混,他说你放学后别走,你走出学校,发现前后七八个小混混把你围住,这个时候你跑是跑不掉的,挨打是一定的,那你该怎么办呢?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你就盯着一个人打,这么多人你肯定打不过,你就对这一个人使劲儿揍,揍到后面他急了,可能转过来帮你拦住别人,说“你们别打他,你们越打他,他越打我”,这就是以寡敌众时的一个策略。
苏轼的“八面受敌”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周围资料太浩瀚了,这么多资料向你涌过来,这个时候你是无法应对的,该怎么办,“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我先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只挑和自己目标有关的东西。苏轼就说,他读《汉书》的时候第一遍只读里面的军事内容,比如就看卫青和霍去病这一部分;第二遍只读经济方面的内容,有的放矢,当你有一个目标之后你去读资料的效率会比你随便翻的效率要高得多,对我来说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要写《两京十五日》,那我去读明代史料的时候,我就紧盯着大运河相关的东西去看,紧盯着宣德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内容。
我会去知网下论文,我知道知网是什么(笑)。当我读完大运河的论文之后,我了解了这事儿和漕运有关,紧接着再去搜索与漕运有关的资料,读完再搜索“漕运+宣德”,这样搜索起来很有效率。
南都:说说你为什么会对历史题材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写历史?
马伯庸:我一开始没想专门写历史文学,我早期文学创作什么都有,历史、推理、奇幻,甚至前两天我还上了一个院线电影,改编自我最早写的一篇恐怖小说,而且是《午夜凶铃》的导演拍的。早期我什么乱七八糟的类型都写,后来我觉得历史比较有意思。
中国历史一个是非常长,一个是它足够丰富,它的历史记录一直没有断过,这是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里面可以挖到所有想要的素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随便找点东西出来都可以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
而且对我来说,写历史还有一个比较“占便宜”的地方,比如我一说于谦大家都知道,一出场不用多介绍,不用我额外描写背景和性格,我一写名字你们脑子里自动浮现他的画面,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历史文学占便宜的地方就在这儿,但是历史文学难也就难在这儿,因为它的情节都是固定的,我又不写穿越,所以我没法改变历史,大家都知道主角死不了,至少这个太子死不了,他最后一定会顺顺当当到北京,会当上皇帝,怎么让读者在知道故事结局的情况下写下去,让你们还愿意继续读下去,是个很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也是个乐趣吧。
南都:由你另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洛阳》即将开拍。从长安、洛阳到两京,这几部作品都以古代都城为题目及背景,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特质或一脉相承的地方?
马伯庸:一脉相承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背后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他们背后都有着生活的文化底蕴,都能和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古代著名人物之间有关系。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显得很厚重。选择这些城市写,大家会产生无数的联想,一提到洛阳大家会想到武则天、七天建筑,提到长安我们会想到开元盛世,提到两京我们就想到朱棣的迁都,北京这边明清两代皇帝,南京这边的金陵种种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能够产生很多的联想。那对我们作者来说,省了很多渲染的功夫,我只要把长安两个字或者金陵两个字摆在这儿,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情怀,这是中国人骨子里自带的一种对历史的亲近感。
南都:《长安十二时辰》推出海外后,也受到了很多日本网友的追捧,剧中呈现的“唐风”在日本引起关注,你认为这种靠影视剧的文化输出前景如何?另外,网上也一直流传“唐代文化在日本”这样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马伯庸: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文化输出的被动者,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盛唐文化,要看日本人怎么来拍,日本那边可能也保留着一些唐代的文化遗存,我去日本的正仓院看到了很多唐朝的文物,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了的,我觉得特别可惜。
其实电视剧也不可能100%还原长安城,剧里的很多场景并不真实存在,但营造出来的效果就很酷。比如,剧里有一个细节,李司丞命令架起“火闹钟”来倒计时,一个时辰之类办完事儿,这个“计时器”是一条龙的形状,下面挂着丝线,上面横着一根香,给人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实际上没有任何古籍记载过这种东西,只是有类似的,但是它的出现不突兀,反而让人觉得很合理。电视剧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设计,可以说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能够有机会自己创作出一个还原中国古代文化的作品,而且变成了电视剧这一种现代人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让国外人接受的方式,这也是文化输出的一种方式吧。
南都:听闻《两京十五日》的影视版权已经签出,你对未来这部影视剧的演员、制作等有何期待?
马伯庸:书的改编权已经授权出去,他们还在前期筹拍,但至于到什么进度,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的习惯是授权之后就不管了,该干嘛干嘛,忙我自己的事。
南都:编剧也没有去找你看吗?
马伯庸:还没有,我完全不管,我就说,你们尽情发挥吧。但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以后,能够把大运河沿线的这些明代很多城市的风貌一次体现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明白,历史上有一条很牛的运河,而且对我国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南都:你认为它能复制《长安十二时辰》的成功,成为红遍网络的年度大剧吗?
马伯庸:我不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言说哪一部作品可以成为爆款,但是我觉得只要认认真真地完成自己的本分,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我相信市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反馈。
南都:你写过明代,写过唐代,你有没有考虑过写写宋代?
马伯庸:宋代我确实没写过,因为宋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艺到了极致,那个时代里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难写,你一写细节就失真了。比如我从来不写李白,不写苏轼,因为写不出来,你只有到达了他们的境界才能写他们,所以难度很大,但也不是绝对不写,除非碰到特别适合的题材。
下一部作品确实在写了,还有一半多,是近代的行业题材,而且这个题材可能之前没什么人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