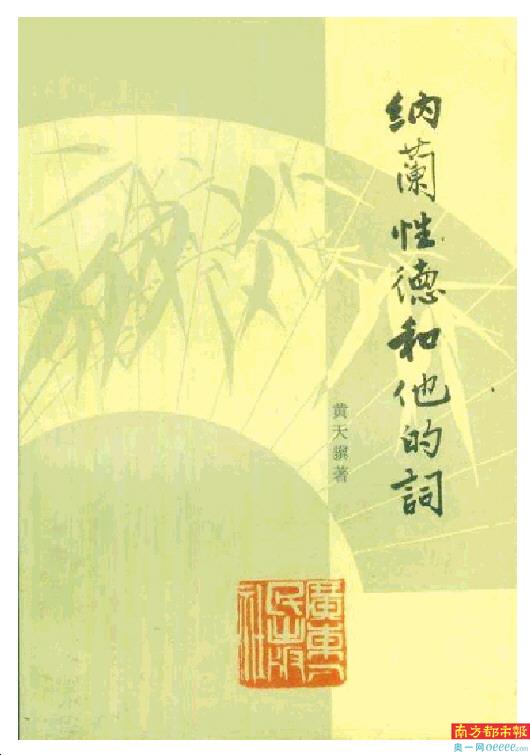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黄天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黄天骥
重阳节到了,现在广州的青年朋友,往往会爬上白云山,登高“转运”。但上了年纪的老广州人,由于祖先墓地多在近郊山坡,则把登高和扫墓结合起来。近世推行火葬,先人的骨灰盒,多放置在银河公墓或俗称“大烟囱”的骨灰楼里,许多广州人便在重阳佳节,到那里祭祀祖先。所以,每到重阳,燕岭路一带,便堵得水泄不通。广州人在重阳思亲之诚的景象,恐怕在其它地方,不容易见到的吧!
重阳节,我也会和亲属前往存放祖先骨灰的地方,虔诚祭扫。墓园里烟光纟因缊,近两年,管理部门虽然提倡不焚烧冥镪,可是,香烛的烟气,依然漫天绕袅。我们首先租占祭桌,摆上祭品,点上香烛,到骨灰存贮楼,捧出先人的骨灰盒,放在祭桌上。我总是把盒子仔细拂拭,也轻轻地打开它,一面观察盒里骨片的颜色,一面忆想父母生前的容颜。然后,晚辈依次鞠躬致祭。我在烟光明灭中寄托哀思,往往会联想到自己写成的第一本论著,关系到我一生学术生涯的过程。无尽的怀念,以及对一个人成长经历的体悟,总在脑海中反复萦回,挥之不去。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所思的“亲”,不仅是父母,也包括培育我成长的先师和前辈学者。
我的母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那时她才25岁。过了几年,我的父亲,因躲避日寇,领着我和妹妹逃难到了澳门。1942年,澳门霍乱大流行,父亲不幸染上,战乱中缺医缺药,两天后即告不治。那时他也才31岁。
先父在抗日战争前,就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父亲在世时,买有不少书籍,包括《唐诗三百首》,鲁迅翻译的厨岛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整套《十三经注疏》等等,足足放满了三四个书橱。小时候,我会拿出这些书乱翻,祖父也要我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可是,在中文系毕业的父亲,除了给我留下不少书籍以外,对我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去世过早,我也只能在旧照片中看到他的容貌,从亲友对他的叙说中,想象他的言行举止。
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广州南海中学寄宿,1952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入住康乐园。留校工作,也在校园里成家,一般只是到了星期天,才回到西关的老家省视。“文革”时,形势严峻,“大破四旧”后,紧接着又和学生们下乡下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更是没有回到老家看望的机会。
在1966年,有一天,我抓紧时间,回到老家看望妹妹,发现家中狼藉得很。妹妹告诉我,前一段红卫兵来“破四旧”,抄捡了不少旧物,连父亲留下的书籍也都搬走了。我对其它失去的东西并不在意,但书籍对我有用,便赶紧察看几个留下的书橱。只见里面空空如也,连版本珍贵的《十三经注疏》,也被“破四旧”者作为四旧搬走。我望着几个空空荡荡的书橱,实在伤心惆怅,但也无可奈何,只有用手掌在它里里外外,四处抚摸,缅怀父亲,也痛惜失去父亲遗下的书籍。
忽然,在一个书橱的内侧,我摸到了一本书。可能是这书紧靠书橱竖着,封底的颜色,和橱内木质相似,抄家者匆忙间没有发现。我赶紧把书掏出来一看,原来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侧帽词》。我赶紧把它放在袋子里,带回康乐园收好,留作对父亲永恒的纪念。谁知道这劫后余灰,竟成为我在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本书,促成我对纳兰性德的研究,写成并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论著《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而我“暴得大名”,又和另一篇论文刊出的周折有关。
打倒“四人帮”后,开放改革,万象昭甦。在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上,开始改变八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本小说的局面。各地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或复办,或新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当时,在东北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横空出世,该刊每期刊载的学术论文,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论文的质量也颇高。这本以“多而杂”为特点的刊物,异军突起,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在1979年秋天,该杂志的主编写信给我的老师王季思教授,约请他撰写一篇评论《桃花扇》的论文。
《桃花扇》是我国古代四大名剧之一,“文革”前,王季思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桃花扇校注》,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文革”前夕,“左”风渐炽,学坛上出现否定《桃花扇》及其作者孔尚任的风气。“文革”结束,需要拨乱反正,《社会科学战线》向戏曲研究权威王季思老师约稿,这很自然,王老师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1979年夏末,有一天王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告诉我关于杂志约稿的事,他说:“你在大四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桃花扇》问题,论文答辩时,三位委员董每戡、詹安泰教授和我,一致评为优秀。后来论文也发表了。因此《社会科学战线》约稿,你先写初稿,我再修改补充,然后联名发表。”我知道这是老师提携的心意,欣然从命,便回家对《桃花扇》潜心探讨。
谁知过了三个月,我还没有送稿给他审看。他有点急了,他知道我熟悉《桃花扇》,而且从来写作速度也不算慢,怎么会迟迟不能写出?后来我把论文初稿呈上,过了两三天,王老师又叫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仔细看了论文,写得很好,超过他对《桃花扇》的理解,因此他完全没有改动,这文章不联名发表了,就单署我的名字。我当然不同意,说杂志是特邀老师写的,老师怎能不署名?他又说,论文完全是你的思路,我不能掠美,已经只署上你的名字,让海燕(王师母)寄出了,通讯地址就写中文系办公室。既如此,我反对也没有用,只好从命。在这里,我感受到老师一心培育后进的高贵品德。
大概过了三个星期,王老师和师母忽然到了我家,兴冲冲地对我说,《社会科学战线》的主编给他复信,对论文评价很高,刊载已不成问题。接着,他把信交给我看,那是用毛笔字书写的信,整整写满四页信笺。我看到信中对我写文章大大肯定,有些话甚至说得很过头;信中还有祝贺王老师能够把学生培养成材之类的话。我看了,交回给王老师。当然我也暗暗高兴,以为鸿鹄将至,就静等论文发表吧!
又过了一个月,我在中文系办公室收到一个用大信封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那篇《桃花扇》论文的退稿。我心想,编者怎么对王老师说得天花乱坠,却又把原稿退回给我呢?这岂不是有心作弄人吗!一气之下,便把退稿的大信封翻转过来,用浆糊粘好,放进稿子,贴上邮票,随手便寄给当时全国文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文学评论》。这事情,我没有告诉王老师,免得引起老人家的不愉快。岂料只过了两个月,我写的《孔尚任与桃花扇》即登载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上。老实说,当年副教授工资不高,我没有订阅期刊。论文在《文学评论》发表后,倒是王老师先看到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家,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好和盘托出。王老师笑了笑,说:“《文学评论》识货,在全国影响更大,你反占了便宜了!”接着,他还叫师母斟了两小杯绍兴黄酒,和我碰一下杯,表示祝贺。后来才听说,《社会科学战线》原准备发表拙作的主编,忽然急调进京,后任者发觉该刊的前两期,已经发表过有关《桃花扇》的文章,不想论题重复,所以退稿。这也无可厚非。
就在1980年夏初,我忽然接到《社会科学战线》毕万忱先生来信,邀请王季思老师和我到长春参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我知道,王老师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所以也邀我参加,我当然从命。到了会上,一看,该刊邀请了十位来宾,除我叨陪末座以外,九位都是名髙望重的前辈大家,如程千帆、郭预衡、杨公骥、张松如、吴调公教授等,他们的著作,都是我在求学时的必读书。我很感谢《社会科学战线》给我亲聆诸位前辈老师教诲的机会。会议结束后,毕万忱先生一再嘱我给他们的刊物奉稿,我也希望有向东北学者求教的机会。当时,我的学习兴趣,已转向清代诗词,考虑到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是东北的满族人,而且我在家里,就有先父遗下的《饮水词》《侧帽词》,便和毕先生确定了这一选题。这论文在1981年写成奉交,随即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上。
就在该论文面世不久,有一天,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校友,忽然领着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来访。当时我家住在三楼,没有电梯,这位老人爬着楼梯上来,显然有点气喘。一经介绍,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名重一时的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重华先生,我知道他是革命前辈,又是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学长。甫坐下,他便开门见山说:“天骥,我今天是特别来向您约书稿的。我刚看过你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论文,很不错。你就按这论文的观点和结构,写成一本论著,书名就叫《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年后交稿。”我又惊又喜,当时就想,年迈的老社长,其实只需托人带个口信,就可以了。但他老人家竟屈尊来舍,让我十分感动。
我对清代历史文化环境和纳兰词,稍为熟识,就在任课之余,抓紧钻研,用了大半年工夫,便完稿了。记得那年暑假,因要写纳兰性德的“交游考”,中文系资料室资料不足,便整天泡在历史系的资料室查阅典籍。这一章字数不多,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那年特别炎热,资料室没有空调,空气也不流通,甫坐下,便汗流浃背。完稿后,我立即送交出版社,并斗胆请杨老赐序,他也慨然允诺。
拙著在1983年出版,据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版社也一版再版。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从前文坛非常看重纳兰性德,人们甚至把他看成是李后主的后身,在词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可是,1949年后,他名声泯灭。记得解放初上海某出版社编印了一本《纳兰词》,不久就有人大张挞伐。此无它,因为纳兰是清代大权臣大贪官明珠的儿子,又充当被皇帝宠幸的御前一等侍卫。而且,他的词作多写爱情、悼亡,情调缠绵悽楚。在强调阶级斗争“日日讲”“天天讲”的年代,谁也不敢去碰他。“文革”结束,开放改革,人们对爱情、友情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有所认识;对作家内心矛盾,也注意不作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不少青年朋友情窦初开,而对前景又颇迷惘。拙著的出版,适逢其时,于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纳兰热”。到现在,人们对纳兰性德的兴趣,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退。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近期出版社又将重版,在重阳佳节临近的时候,我打开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思前想后,领悟了人生的许多教益。
当初,我拿回幸存的《饮水词》《侧帽词》后,只把它收藏在书架上。等到答应给《社会科学战线》撰写有关纳兰的论文时,才把父亲遗下的这本书找出来细读。在书里,发觉先父没有留下一个字,却在一些词牌上方,用铅笔划了一个圆圈。我细看那些划了圈的词,全是纳兰的悼亡词。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买这本书,是为了寄讬对我母亲的哀思。我读着这些词,想着父母之间的爱,也萌发思亲之感,不禁泫然欲涕。当然,为了研究纳兰词,我只能收拾思绪,反复阅读。一边读,一边随手在书上用红色圆珠笔记下自己的心得。后来,拙著出版,有人也看到了我父亲遗下的本子,以为上面的批注是我父亲写的,以为我“剽窃”父亲的“心得”而又不作说明,起码有“不孝”之嫌。
其实,只需细看,书上的批注全是我的手迹,用的也是简体字。而在先父生活的年代,根本不存在使用简体字的可能。想到诮谤者的疏忽,也只好付之一笑。不过,我倒真希望父亲在书上留下批注,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让我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读书人对纳兰词的看法,这也许会使拙著写得深刻一些。可惜,不知先父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有写?思前想后,思亲之情倍增。
再想下去,许多培育和提携我成长的老师和学界前辈,也不都是我应该思念的亲人吗?不错,父母给我血统的承传;而学术前辈,给我是师德以及为国育材,扶持后辈良好品德的承传。从我第一本拙著成书的周折过程中,可以看到,不知老师们和编辑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从王老师对《桃花扇》论文的不署名,《文学评论》对论文的迅速刊发,促成《社会科学战线》约写有关纳兰的论文,再到杨重华社长的亲自督促,这才催成拙著的产生。记得先师王季思教授对我说过:“一本书、一篇论文的刊出,编辑同志有一半的劳绩。”言犹在耳,不敢忘怀。
如今,在重阳节到来的时候,我还能对着先父的骨殖拜祭,但是,王老师的骨灰远在温州;对我影响至大的董每戡、詹安泰以及杨重华等老师,也陆续仙逝。秋风瑟瑟井梧残,重阳佳节倍思亲。我只能对他们一一感恩,望空怀想。
思亲、感恩,是家国情怀的一个方面。希望从古以来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能够永远承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