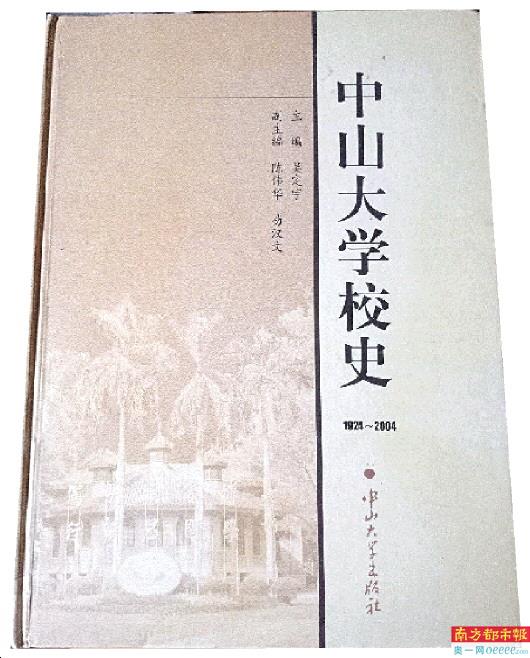
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
陈平原
我的三位中大导师中,吴宏聪先生最为长寿。就近照顾耄耋之年的吴先生,成了定宇兄的重要责任。每回电话联系或登门拜见,吴先生总是对定宇兄及其弟子的尊师重道大为赞赏。有此古风犹存的师兄,让我这远在天边无法执弟子礼的老学生,不禁心存感激。说实话,这也是我与定宇兄比较亲近的缘故。
我的硕士学位是在中山大学念的,导师为吴宏聪(1918—2011)、陈则光(1917—1992)、饶鸿竞(1921-1999)三位教授,那时强调集体指导。198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课程,马上有了四位师兄——吴定宇、邓国伟、王家声、罗尉宣。可惜五个月后,这中大中文系第一届硕士生就毕业了。四位师兄,两位留在中大任教,两位到出版界工作。先后出任广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及《同舟共进》杂志主编的王家声,因约稿多有联系;但接触最多的,还是留校任教的吴定宇。
三年多前,定宇兄不幸去世,我在唁电中称:“犹记1979年秋天,作为二年级本科生,我接待新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曾帮定宇兄扛过行李。日后因师出同门,虽南北相隔,来往依然密切。近四十年来,师兄弟不时交流读书心得及著作,何其幸哉!”(参见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2017年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之所以四位师兄中,与吴定宇来往最为密切,仔细想来,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八十年代后期,吴定宇兄住陈则光先生家隔壁楼,我每次回中大探访导师,都会顺便到吴兄家坐坐。记得有一次定宇不在家,他那聪明伶俐的儿子,那时才四五岁,倚门而立,摇头晃脑地答道:“断肠人在天涯。”我大吃一惊,还专门向定宇兄建议:让小孩背诵古诗词是好事,但最好挑明亮点的。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孩子半懂不懂,随口而出,情绪一点不受影响。
另一因素是,他指导的首批博士生陈伟华,日后到北大跟我做博士后研究。关于他的导师吴定宇以及导师的导师吴宏聪的故事,是我们聊天时的绝佳话题。至于师兄的身体状态以及两次撰写陈寅恪研究著作(《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的具体经过,更是被他的弟子时常念叨。我因而也对早就远去了的康乐园生活,以及中大近年学术发展,有了更多贴近的体会。
我的三位中大导师中,吴宏聪先生最为长寿。就近照顾耄耋之年的吴先生,成了定宇兄的重要责任。每回电话联系或登门拜见,吴先生总是对定宇兄及其弟子的尊师重道大为赞赏。有此古风犹存的师兄,让我这远在天边无法执弟子礼的老学生,不禁心存感激。说实话,这也是我与定宇兄比较亲近的缘故。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俩学术兴趣相近。都不满足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日后拓展到学术史、教育史等,故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二十年前,定宇兄编《中华学府随笔·走近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给我提供了撰序的机会。那时我正热衷于谈论中国各大学的历史及精神,涉及中大时有点犹豫。因为,“我对中大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就读康乐园的直接经验”;依赖直接经验者容易一叶障目,“念及此,我方才有意识地在关注母校现状的同时,收集、阅读、辨析有关中大的历史文献”。恰在此时,定宇兄布置作业,使我有机会好好补课,日后再谈母校,才不至于荒腔走板(参见《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走近中大>序》,《万象》第1卷7期,1999年11月)。
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选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并撰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既赢得不少社会声誉,也带来了许多困扰——尤其是在校内。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在《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的“代自序”《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中,我谈及:“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这句话埋藏很深的感慨,但略有瑕疵,因为,好的“校史专家”同样能从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的夹缝中破茧而出——此事端看个人道行。
没想到师兄比我更勇猛精进,居然承担起主编校史的重任。中大八十周年校庆众多纪念图书中,我最欣赏的是黄天骥的《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增订本】,2014)、金钦俊的《山高水长:中山大学八十周年诗记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这册《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比起此前的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一直写到当下,实在是勇气可嘉。中大校史上的敏感话题比较少(相对于北大),这固然是一方面;时任领导的信任以及环境氛围相对宽松,也是无可讳言的。
李延保书记在《中山大学校史序》中提及这所名校曾组织过多次讨论,确认中大人三个明显特征:民主精神、务实作风、爱校情结。“她因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文化。要理清中山大学的自我发展体系,要整理其中的精神气韵,确非易事。”所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既呈现为贡献与辉煌,也包含失落与沮丧。我在《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以北大、复旦、中大为中心》(《书城》2016年第10期)中提及,“讲述或辨析大学故事,虚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固然是一个障碍;但这属于技术层面,比较好解决”;真正困难的是如何面对“校史坎坷的另一面”——“大学故事若彻底抹去那些不协调的音符,一味风花雪月,则大大降低了此类写作的意义。”
我的导师吴宏聪先生长期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对中大历史上的坑坑洼洼洞若观火。因此他给《中山大学校史》撰序,称“我觉得1949年至1976年这一段校史最难写”。吴先生表扬该书第四编第四章“该章对其利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编撰者的史德,同时也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提供认识”,那是真正读进去了。其实“文革”十年相对还好写些,因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准绳;反而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高等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戕害,不太好描述。如第四编第二章“雨霁风清”的第三节“教学与科研”(263—271页)以陈寅恪为中心展开论述,且全文引用《陈寅恪自述——对科学院的答复》,很能体现编撰者及审读者的胸襟……
编撰校史需搜集及鉴定大量史料,不过这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做到;反而是既体现对于本校历史及传统的呵护,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如此学术立场及趣味,很难实现。该书属于集体项目,各章节水平参差,功劳及过失并不全归主编;但定宇兄工作十分投入,逐章逐节修改,还是下了很大功夫(参见该书《后记》)。我翻阅过不少中国大学的校史,深知此事大不易。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兄能有如此业绩,值得铭记。
2020年10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潮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