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云 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广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此岸到彼岸的泅渡》《南方与北方》《理智之年》《欲望之年》《赴历史之约》《寻找失踪者》《我的痛苦配不上我》等。最新出版散文集《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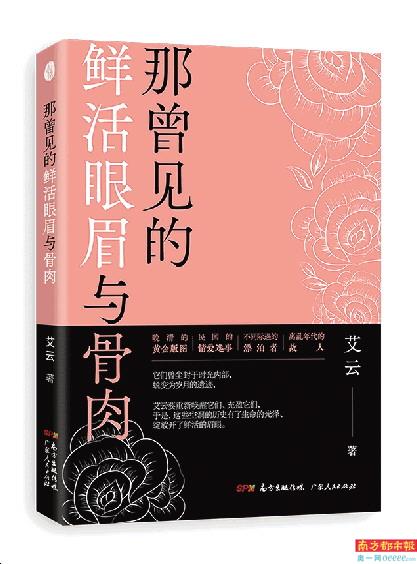
□ 王晓娜
灵魂有纹理吗?可以被摹状和雕刻吗?那在时间的倥偬中,刮过的某阵风,下过的某阵雨,可以被钩沉和演绎吗?我读着艾云的文字,读着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分明听到有风吹过,有雨飘过,有光闪过,有声音从文本间流淌而来——那是庖丁解牛时金属刀具与牛骨碰撞发出的声响,宛似一场场生命的独舞,为糅在历史和岁月中的事件,为消逝在季节和时间中的英雄,抑或平民。
我感到我被拽曳和顶托着,和艾云一起,去看那黄河翻滚、槐香漫溢的开封古城和市井民间,看那漫长严冬中的苦寒北国,看那被湮没在历史沟壑中的烟华往事,看那些被抛弃被遗忘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命运遭际所呈现的存在和意义。
艾云对艺术的敏锐感觉,源自对心灵沃土的耕耘。她是一位忠实于心灵的作家,她从“人”出发,写诡异博大的人心,写幽微复杂的人性。《乱世中的离歌》写民国时期,作为陈西滢妻子的凌叔华与武汉大学英籍青年教师朱利安的一段风月往事,艾云以女性敏锐的笔触摹写了一代才女凌叔华出轨朱利安前后的犹疑纠结、欢乐痛苦和焦虑失落。艾云说:
事实就是真相。……天下无新事,原本都是同情同理。……这不是一段艳情,不是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桃色轶事,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隐情,让人有钻心的疼痛。如果你不是简单化潦草处理问题时,你会感应到。
是的,她用温润的笔,抚顺一地鸡毛的琐碎纹理,呈现高高在上的优雅的精神,呈现人身为人的尊严;她尊重灵魂的真实样貌,向人性致敬。
在《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一文里,艾云写到一系列关于河流的故事,写到江岸上的一个女人,与一个撑船、逐江水漂泊过活的男人,在江边租屋、晓风残月下“金风玉露相逢”的尘事:男人宽厚的胸脯、高扬的脖子,女人柔软的腰身、明媚的眼眸,照亮彼此苦寂庸常的岁月和生命,即便男人最终“生死未卜”,杳无音讯,即便“女人已经走向风雨兼程的歧路”,那又如何,女人用“不合礼法”之勇敢换取男人之“舍得”的“民间规矩”,已然天经地义,正如艾云一语中的:
我原本想写的就不是人类整体性那历史概括的恢弘主题,而是想触及个人的时间。这可持续的和不可持续的时间里,那些眼眉,那些骨肉,那么的鲜活、生动。
在这样的表述里,我们不难读到艾云的内秀敏感:她是如此注重内心的感觉,总是如实又不失优雅地呈现人物的灵魂质地和生命状态,捕捉所有关乎“在苍茫的水面,一个人的救赎”的故事和人物。种种这些,到了她的笔下,都闪耀出短暂抑或恒久的灿烂光芒。
这部由六篇大散文构成的书,其他篇章还有《黄金版图》《民间在哪里》《缠绊不清的男权》和《美学生活》。艾云的诗性语言和智慧思考建构起她具有哲辨气质的文本,这正是她写作伦理的异质性所在。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仗剑天涯的侠者,戍守边疆的戴枷囚徒、举世瞩目的虎跳峡朗保罗们,还是开封古城街巷中的引车卖浆者流,抑或逐水而居的族群、马上倥偬的王朝,乃至背井离乡的广州移民者、象牙塔里的历史学教授,聪慧敏感如艾云,自然看得到他们身上有光,眼底有大义,内心从容——这是启亮晦暗人世和庸常人生的点点灯火,是穿透暗霾沉雾的黎明曙光。
出生于开封古城的艾云,似乎继承了这座世界级文明古城高贵典雅的文脉:她对语言的要求极高,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语言的传承创新,又在大量的阅读中积淀了深厚的西学功底,这使她的语言呈现出“诗性+智性”的特质。她热爱西方哲学和文论,但她的写作从不卖弄理论,不故作高深,她以低调澄明的心境、贵重的操守良知作为如诗文字的背景,将自己的思考对读者和盘托出;她童年劳苦,对贫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深谙“渺小即伟大”的真理,因而她常常心怀古城,眼望星空。
艾云擅长虚实结合,以温和宽容的方式将矛盾对立的双方联系起来,为诗性语言与智性思考打通启应的桥梁。比如,“她们站在时间的悬崖,不知能否理解女人的生命就像那无奈的风,一阵吹过就场光地净了”“女人不会找这种价值判断还停留在史前时代的男人交往,她不会自取其辱”“这主要是女人独立判断了,而男人又跟不上女人的高度”(《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
再如,“海德格尔对她(汉娜·阿伦特)的成就故意不睬,而她则尽可能找机会去见他。哪怕在他们交谈时,门缝里是海德格尔妻子那双窥测监视的眼”(《美学生活》),“上帝用格外的恩宠,抚平她们身上的时间印痕。那印痕曾经带给一般女人斧砍刀凿的残酷。她们躲开了,获得了比年轻貌美更灿烂夺目的东西”(《缠绊不清的男权》);
又如,“这些人在精神的高蹈中去思人性、历史幽微与奥秘,他们对世界文明越有贡献,他们的灵魂越壮阔,则越可能肉身孱弱,离自然本能远之又远”(《乱世中的离歌》),“民间在哪里?它就在普通人家飘来的一阵阵泔水味里,在推车串巷叫卖的吆喝声中,在男人们叼着烟卷逗鸟的单纯神情里,在女人们晾晒衣物时手臂上扬的姿势中。……民间远离庙堂,毗邻江湖,紧挨乡野。民间演绎的,从来都是不必虚构,就能吸引人心的生存故事。民间有太多心酸难熬的事情,想想,就得放下,不放下怎么办?人总得活着。民间因此相信传奇,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民间学会的是祷告,而不是诗歌与哲学的讨论”(《民间在哪里》);等等。
如此充满诗性和神性的语言,在艾云的笔下汩汩流淌。她奉黄河的使命,用冷厉的热眼,去追寻被冲刷至岸旁和沟底的沙砾,去抚触个体命运的纹理。时间的风走过,不着痕迹,历史人文的“鲜活眼眉和骨肉”扑面而至,栩栩如生。
艾云是当得起“思想者”之称号的,她对文本思想性的叩问和追索,源自她心底一直葆有的怜惜与宽容、悲悯与厚道,她替世间的一切物事欢歌、哭泣、叹息、喝彩、无奈、忏悔,她在字里行间修筑起一座“修道院”。无论是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情感纠葛,还是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爱恨缠绊,抑或开封街巷里的医生吴清奇与女病人之间的八卦轶闻,抑或者某个不知名女人与某个不知名土匪的一段露水情缘,艾云都从不粗暴定义,而是理智冷静又满怀疼惜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听由人物随情节和灵魂自由生长。
在《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一文中,艾云写到对“丛林与都市”的思考。丛林代表最原始的非文明部落,都市具有“智力属性”,强调和遵循文明法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历史的进步,随着都市的现代化发展,文明真的在全方位进步吗?人性和观念真的有所改益吗?人类的原罪和原欲是否还停留在丛林时代呢?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婚姻缠绊,又到了怎样的阶段?——
都市在工作的意义上给女人以施展的天地。她们在不那么在意男人的目光时,……决心不再让自己像那红果一般饱满结实地挂在树枝上。……而男人则在女人和历史的双重目光盯视下,浑身更加不自在起来。
对于这些千古难题,艾云耐心探讨、层层剖析,并未给出答案和注脚,一如生命本身的“无解”一样,在历史和命运的吊诡安排下,只有无言是对的……
史河蒹葭,文脉绵延;沧桑山河,草木春秋。艾云的思想,艾云于文本间构筑起的“修道院”,脱不开她对命运的抽丝剥茧,脱不开萦绕推曳着她的“忏悔”心结,脱不开她广博的救赎情怀。艾云的写作是有野心的,她敬思想而不耽于其中,沉迷于剖析自身又能够及时跳脱,她从自我透视他者,透视每个生命个体的存在,进而去抚触人类整体命运的肌理与褶皱。
在《缠绊不清的男权》一文里,艾云写道:
新时代的男权,使男人对生命有敬畏,对人性有敬重。他们曾经活过的证明,恰恰是在异性那里。……生命放进去,就是性别放进去,他们希望女人快乐、幸福,否则的话,自己的生命将无声无息,毫无乐趣可言。……在细细密密、真真切切的生命故事里,男权不指向政治,女权也不再指向运动。生命个体的讨论,必须先要悬置道德与伦理,……本来,这些东西就像蔓蔓芊芊的水草,在生命的深渊中缠绊不清。
在《乱世中的离歌》一文最后,艾云如此评价陈西滢:
这个有些冷漠的人,是不讨人喜欢。可他总在说出自己真实的主张……他不想冤枉别人。他在放过别人吗?没那么样的高风亮节,他只是想善待自己。无论在政治或是情感处理方面,都是如此。
如此热情而冷静,宽容而公允,这便是艾云。随着挖掘和呈现,她常常把所谓美的、符合道德的事物,置于显微镜下,让读者看到其千疮百孔的真相;也把所谓丑的、见不得光的事物,置于显微镜下,显示其局部的绮丽壮美。艾云深爱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每一丝感觉,写男人和女人之间诡谲的欲望和战争,写其建立在罪恶土壤上的高尚的情感,写生命个体在微妙事件中的“两难”处境——而这处境,何尝不是伴随于所有人生命中的伤筋动骨的疼痛?不正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命运和遭际吗?
写至此处,我仿佛看见远离豫乡故土、坐在粤地花城雕花窗棂下的艾云,正饮下醇香的陈皮酒,提气,凝神,酝酿,至微醺状态,写下如牡丹花般散发着高贵、优雅清香的文字——有黄河流动的气韵:意境朗阔,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可摹状落日与旭阳同在的场景,亦可拥抱寂静澄明的光辉。从黄河岸到珠水边,艾云埋头写下的文字,却如她高高盘起的发髻,诗意飞扬,精神高蹈,照亮灵魂和命运的理纹。
◎王晓娜,编辑,现居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