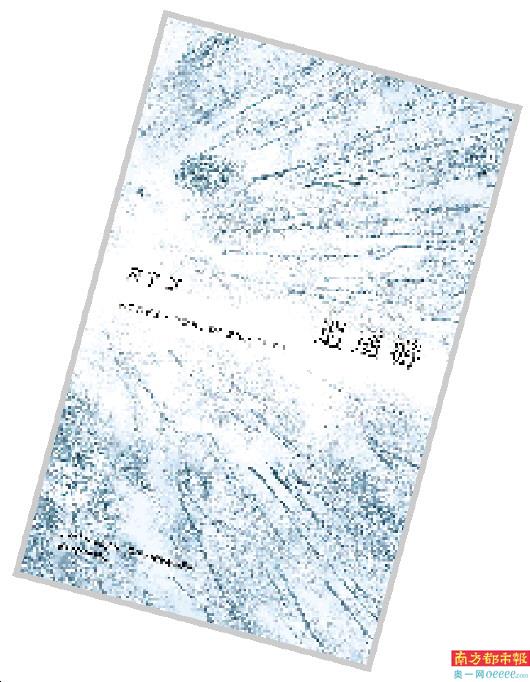
《逍遥游》,班宇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版,58.00元。
□乔纳森
班宇的新著《逍遥游》,与他的上一本短篇集《冬泳》相比,差别不小。简单一点说,我们不妨把《冬泳》中的六篇小说称为“现实主义”的,或者至少还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到了《逍遥游》这本书,一共七篇,恰好目录上排在奇数位置的四篇,即《夜莺湖》《蚁人》《安妮》《山脉》,都程度不同地脱离“现实主义”手法了。最后的《山脉》,用了拼贴的方法颠覆叙事,不仅把外衣脱了,简直把衬衣也脱了。
那么,《夜莺湖》《蚁人》《安妮》的手法属于什么性质呢?我觉得用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派名“超现实主义”来概括容易引来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我宁可管它叫“超越现实主义”。超越现实,就是指,从现实这扇门进去,从非现实、不现实的门出去。打个比方,就好像你坐上一辆出租车,结果车开得越来越快,渐渐腾空离地,冲上云霄。这种手法,其实并不是班宇独有的,而是不少当代青年作家都尝试过的,例如近年的双雪涛。像《蚁人》这一篇,我猜,如果被印到双雪涛去年的短篇集《猎人》里,估计没几个读者能觉察出异样。事实上,我们都明白,假如一种新的艺术手法可以在不同的艺术家间通用,而出来的效果又让人分不出来是张三还是李四,那么可能这就不再只是个别艺术家的问题,而是这种手法本身的问题了。
事实上,“超越现实主义”的念头,绝不是新冒出来的。左拉在谈他自己的作品时就概括得很好:“从精确观察的跳板一跳,就跳到了星空。真实向上一飞,就变成了象征。”一跳就跳到了星空,几乎已不再是比喻了,它就在字面意义上落实到班宇的小说《安妮》里:“一团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穿胸而过。
不过,在近年的双雪涛、班宇那里,“超越现实主义”的缺陷暴露得已十分明显。毛病不在于“超越现实”本身,现实当然允许超越,其通病在于,从现实到非现实的路,走得不自然,有时可以说是很任性了,想跳就跳,想飞就飞,没把“非现实”当回事似的。我们常说,要正视现实、尊重现实,其实,对“非现实”也要尊重,把“非现实”表现得如同现实一般,是需要高超的艺术手腕的。而且,仅仅靠艺术手腕,把“非现实”在场景上描绘得真实可感,也还远远不够,甚至像在村上春树一类的作家那里一样,变得有欺骗性、乃至有害。“非现实”,必须首先在心理上、进而在社会的整体情态上,是令人信服的;若它是一种飞翔,也应该是滑翔,是一种你只要稍稍助推一把,就能自己飞出去的东西。卢卡契对左拉们所做的批评——“隐喻被膨胀为现实”——今天依然有效。当然,像班宇的《夜莺湖》,“非现实”自有一种迷离的、闪烁的魅力,但如卢卡契所说,其主体还是来自“一种偶然的特征,一种偶然的类似,一种偶然的情调,一种偶然的凑合”。也就是说,今天的“超越现实主义”带着随意的特征,乞灵于偶然凑泊,而非真正的更高的凝聚与契合。在双雪涛的《猎人》中,这种弊病尤为显著。
班宇的现实主义笔触,几乎总是出色的。尤其是人物对话部分,第三人称间接引语的运用、语气节奏的把控,十分高妙,中国年青一代作家里可称独步。这种自然、通脱的文笔,为小说营造了一种极其自然的日常氛围,便于作者将读者引向他幻化出来的“非现实”。可是,像在《夜莺湖》里那样,一旦我们被引入“非现实”,读到“一条或者几条大鱼,在身后的池里持续跃起,争论不休,溅起无数水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藏在荷叶深处,一直朝着我们扬水”这样的句子,我们不能不马上从之前那种极其自然的日常氛围中醒转过来,立即从生理上获得一种非真实感,从而意识到作品在从现实进入到“非现实”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断裂。
在小说集《逍遥游》中,可以被归入“现实主义”组别的三篇分别是《双河》《逍遥游》《渠潮》。《渠潮》是一次尝试,尝试构建出一个作者自己并没有经历过的八十年代。从构建的角度考察,针脚细密,情势熨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与许多读者的印象相反,我没感到这篇小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叙事过于传统、迂缓,没发挥班宇爽利的长处,人物缺乏深度,动机模棱两可,总之,是较平淡的一篇。《逍遥游》一篇,自然是极精美的,属于那种任何读者都不可能错过、不可能不为之触动的佳作。《逍遥游》的精神内核与外在形式,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平衡,它成为班宇的代表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依我个人的感受,整本书里最令我读后萦怀的却是《双河》,是发生在一个中年男性与离了婚的前妻、不在一起生活的女儿以及几个朋友之间的简单故事。《双河》的叙述甚至显得稚拙,平铺直叙,有点像外行写的,但实际上,“剧中剧”的嵌入、结尾的往事追述,俱见班宇在结构上的精心布置。抛开这些不谈,从精神的成色来说,这一篇也是最结实的,最没有杂质,平静,沉着,却暗涌不断。可矛盾的是,《双河》却几乎是最不“班宇”的班宇作品。班宇以往的抒情气息,在这一篇里汰洗得最干净。这就不能不使人好奇:班宇接下来会沿着《双河》的方向走呢,还是会朝《夜莺湖》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逍遥游》《双河》中都有一段旅行的记述,而在《冬泳》一书里,《空中道路》那篇的旅行记述,同样予人深刻印象。班宇写旅途,把精神的松弛、把那种飘荡感写得特别有味道,在当代作者中,我还没有读到过哪一位这么擅长写旅途。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空中道路》《逍遥游》《双河》有一种中国古文小品的气息,至少在旅行的段落中,它们是散文化的,散淡,没多少点染,顶多旁敲侧击,气韵流动而不滞。这是中国文学伟大传统中相当独特的部分,看到班宇或于无意中得之,令人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