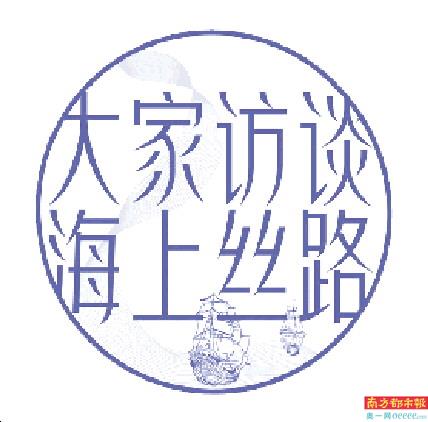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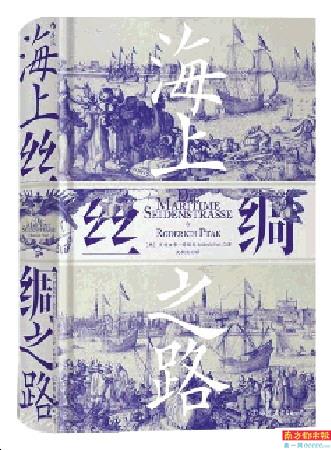
《海上丝绸之路》,(德)罗德里希·普塔克著,史敏岳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10月版。

罗德里希·普塔克 (Roderich Ptak),加拿大贵湖(基芙, Guelph)大学经济学硕士,德国海德尔堡(Heidelberg)大学汉学博士和habil.学位,1986年副教授,1991年Heisenberg 奖学金学者,后来成为德国美因茨(Mainz,Germersheim)大学教授,1994年以来在慕尼黑 (Munich)大学任汉学教授,发表过有关中国文学、海运史、历史地理、澳门历史和中国古代动物史的论文及著作(见www.sinologie.lmu.de)。
历史上中国很多时期
对海洋非常感兴趣
南都: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的沙琬先生1913年提出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你认为研究的充分性如何?是否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了?
普塔克:从理论上说,许多观察角度和研究领域都可以统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但在根本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交流”这个概念是可以扩展的,比如把它和现代的沟通和互联网联系起来,因为沟通也和航线知识及思想交流密切相关。但我们还是先不作扩展,停留在这个核心概念上。我们需要问的是:在研究亚洲和东非沿海各地不同历史及文化的那些专业里,“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专业已经走得比较远,而有些还比较滞后,这实际上取决于观察的视角。
就“海上丝绸之路”这个主题进行写作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是从海洋出发观察大陆的,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他们把各种文化连在一起,跳过了政治及其他因素构成的边界。换句话说:他们并不一定把人在海上的影响和作用归结于各个大陆国家的利益;这些历史学家对于各个政权的命运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把不同地点和不同群体相互联系起来的东西。我认为,在这方面走在比较前面的是中国、日本、法国和葡萄牙历史学家;而英语世界发表的著作就不是这样。
南都:海上丝绸之路是建立在海洋之上,路径难寻,遗存不多,你觉得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难点主要在哪些地方?你有哪些独特的发现?
普塔克:如果把交流——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交流——放到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的中心,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以下的问题:相距非常遥远的地方之间往往存在接触,船只也经常驶过漫长的距离前往目标港口。相关的文本也是用非常不同的语言写成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只了解较少的数种语言,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实际上,即便是纯粹语言学层面的问题也不容轻视。某些词汇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比如动植物或商品的名称等,就发生了转变,适应了其他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本来必须同时是“语言学家”。另外一个难点是要准确地把考古学和来自传世文本的知识结合到一起。
为了研究各种古代文明的日常文化,考古学家在今天要使用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兼顾所研究时代的饮食习惯、疾病、短暂的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因素。对于海上联系的重构而言,这一切可能都很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必须调整自己,适应许多新事物,但这并非对每个人来说都那么容易。
你问到了我的“发现”。在这方面,我必须保持谦逊。我并没有发掘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趣和关切主要是把中国和欧洲的文献和资料结合到一起。
南都:和贯穿中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比起来,你的研究显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资主要是什么?是什么物证或者文字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普塔克:欧洲、非洲和亚洲之间许多商品的交换都是通过海陆两种方式进行的。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的数字。直到中世纪晚期开始,这方面的资料才更丰富一些。然后我们才清楚,某些纺织品、胡椒、丁香、苏木等货物大多以海运的方式交易,而对一些药用产品,如沉香、茴香、麝香、龙脑香等,我们了解得就相对少一些。有些商品极其昂贵,因为运输量少,几乎没有占用船上的运输空间,其贸易具有数量少和利润高的特点。如果涉及到这些商品的使用,那么中国的文本就非常重要了,比如说本草类的书籍。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我们就有了补充信息,也有了更多的数据。
在某些时期的贸易上,白银、黄金和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也必须兼顾来自海洋的一些产品,比如货贝。贝类的壳被作为货币来使用;这种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影响了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云南的货币体系。我们发现中国的远古时代就有贝壳货币。
动植物和动植物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我的印象是,这些东西对日常生活和当地文化来说往往比其他东西更重要。谈到日常生活,对于地中海的各种文化而言,葡萄酒和橄榄的传播是一个影响十分深刻的元素。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中国的某些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比如槟榔的流通,槟榔在医药、仪式、赠礼等方面的使用等。此类现象在沿经过中亚的陆上商路地带就不存在。
你问到的相关文字证明,一直到15和16世纪,如果涉及南海地区及环印度洋某些地区,汉语文献是最重要的。当然,就环印度洋地区而言,我们还必须算上阿拉伯和波斯的材料。从16世纪开始,又多了葡萄牙语的作品,以及不久以后其他欧洲人的著作。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汉语和欧洲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在当地语言(如印度各语言)写成的此类作品中是找不到的。马来文的文本大多形成于更晚的时候,而且经常以口头流传为基础,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不一定可靠。不过,在东南亚等地,我们在各处都有发现很多铭文类的素材,可作参考。
南都: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非常传统的农耕文明,对海洋的探索热情并不高。这种判断是否有局限性?为什么?
普塔克:确实,中国文化始终受到农业的深刻影响。但大多数其他文化和国家也是如此。农业社会和封建结构是一个整体。简单地说,在历史上,单纯以海上贸易或交换为生的地方及文化并不多。即便有这样的地方,也经常是出于某些原因而被腹地孤立的港口。
另一方面,在某些时代,尽管农业很强势,中国仍然对海洋非常感兴趣,对航海也很开放,而且这样的时代比我们所相信的要多得多。古代的吴、越,包括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期间南方的许多小王国,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即便是宋明时代,海洋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也取决于视角。比如《山海经》说“闽在海中”,这个短语就说明最早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东亚的这个地区的。另外,散见于两汉三国时期各类文献的线索也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很准确,而且也和遥远的地方保持着交流。在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当中流传下来的一些文本片段则说明学者们尤其对东南亚非常了解。还有,如果没有广州和泉州等港口,就完全无法想象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说中国始终只是一个忙于自身事务,忧虑北方边界安全的“农业大国”,这样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再符合今天的理解了。
海上丝绸之路
体现着人类之间的信任
南都: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途经南海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或者当地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可否用几个例子来阐述?
普塔克:有些药用商品来自东南亚。它们曾经影响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日常文化。当时,对于这些货物,就和对几乎所有进口产品一样,政府是征税的;而税款就可以作为投资回流到经济之中。明代,今天泰国的苏木和加里曼丹岛以及苏门答腊岛的胡椒大批量地流入中国,流到经济系统之中。
另外一个例子,从拉丁美洲经菲律宾的马尼拉进入中国的白银,在货币体系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进口商大多是福建商人。同时,除了马尼拉之外,福建商人还和日本、琉球群岛、东南亚的许多港口存在交流,这增加了福建的财富。
在别的情况当中,来自国外的需求很重要。比如,在清代早期,欧洲人对茶叶有了更大的需求。这推动了福建地区的茶叶种植,导致当地的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运输行业产生了影响,因为茶叶必须从产地运到交易地点,福建的茶叶往往运到广州。在广州,福建的富商很快就控制了对欧洲客户的一部分茶叶贸易。
其他的例子就是各种纺织品、广义上的陶瓷、艺术品以及家庭用具的生产。某些手工工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满足国外的要求了。从明代开始,这一趋势变得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对某些产品的需求上升,在中国推动了相关产品在技术和生产组织上的改变,也就是促进了创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生产者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曾经存在于中国沿海的各地。
南都:如果要给这条无形却又真实存在长达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做一个阶段的命名,你会如何来划分?依据是什么?
普塔克:给历史划分时期始终是一个问题。对“海上丝绸之路”而言,也不例外。稍微读一下博亚尔(Philippe Beaujard)关于印度洋历史的大作[《印度洋的各世界》(The Worlds of the Indien Ocean)],我们就会发现要给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是多么复杂。关于约公元600年的这段时间,存在许多争议,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各有论据。这个时间点之后,从公元600年到约900-1000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文化的端点:一边是伊斯兰教影响下的西亚各帝国,另一边是唐朝。
我的印象是,从大约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对许多航线的“运营”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元代及郑和的航海活动可以归纳到同一个时间段里。但也有论者认为郑和及其时代应该和此后的时代连在一起。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随着尼德兰人和英国人的侵略性登场,“海上丝绸之路”周边的众多经济和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葡萄牙人似乎看重传播信仰还胜过重视生意,我们不能把他们和其他欧洲人混为一谈。但很多历史学家都还没有理解这一点。
你提问中谈到“一条无形却又真实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和自然可见的街道与铁轨不同,海上航线在这个意义上并非真正存在。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其存在,因为它和相关知识及信息的流通,和人类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相关。由此,我们又一次进入了文化交流的领域。也许,和陆路的“经营”相比,海上航线的规律性“运营”对可靠信息的依赖性要强得多。可能这也意味着,海上的成功要以人类之间更大的信任为前提。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证据,证明了人类相互之间和睦相处的根本能力,只要人有这个意愿。
广州在海上丝路的地位非常重要
南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你认为广州在这条路上的作用如何?为什么会形成它的特殊作用?
普塔克:广州在历史上变得重要的原因有很多:它拥有腹地广阔的入海口。通过众多河流以及其他道路,广州与大陆腹地之间有着良好的联系。广州曾经是割据政权以及地区的首府,为许多人提供了商品贸易和人际交流的优越条件。这符合当地机构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在很多时期,广州还生活了大量的外国人,其开放性是中国内陆城市难以比拟的。
从广州出发,我们可以相当方便地经过陆路前往中国中部和北部。使节们很懂得利用这个条件。而且他们也经常记录下广州的富庶。早期的葡萄牙语文献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时,从广州出发,往肇庆方向还有一条轴线通往西部。这也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纽带。最后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广州,加上东莞和香山(中山)以及伶仃洋里的小岛,可以作为通向东南亚的门户。使节和商人经常从此处入海,前往陌生的港口。一句话,广州是一个交通枢纽,给城市带来了便利。
另外,在过去几百年里,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增长很快,其速度超过其他地区。这既能为出口生产更多商品,同时又产生了对外国商品的更大需求。在某些时期,人们出于经济或其他迫切原因,经过广东而远走国外。当这些人在国外富裕之后,就试图支持仍在中国的亲戚,使资金流回故土。就人口和海外影响力而言,广东很长时期是中国沿海地区中最强的。
说到这里,如果回溯古代,就会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广州相对于泉州的优势有哪些?这对“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发展又意味着什么?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无法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深入讨论。
南都:在你的研究成果中,中国有哪些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节点?他们各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普塔克:正如刚才所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广东省之外,值得一提的有今天的扬州、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漳州和厦门等城市。另外,我们还得考虑几个岛屿,比如舟山群岛的某些岛屿。还有福建和广东交界之处的南澳,也算有一席之地。但只要是清代之前的时期,我们几乎都没有数据。因此,进行这方面的比较有些冒险。而且,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位置更偏北方的,主要位于山东沿海的港口呢?“海上丝绸之路”往东北方向的延伸有多远?对此,日韩的同事们肯定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内容都取决于不同的阐释。
回到中国南方,如果涉及广东和海南,人们首先会想到广州,也许还会想到澳门。但从古至今,伶仃洋地区的地理已经发生了变化。零星的岛屿可以作为锚地,那么对于非法贸易来说,这种岛屿得有多么重要?在这里,我尤其会想到香山县(现中山市)。古代地方志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从前是一个比较大的岛屿,拥有许多难以控制的海湾,住着多文化的族群,类似于后来澳门的早期模板。在去广州的路上,外国人也有来香山的。对于上川岛,我们也可作类似的思考,但如果要确立一个清楚的概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当然,也有的地方更具有某种本地意义或特殊意义。可能海南的文昌就属于这一类。这里的交往出现在小商人和去南海诸岛捕鱼的渔民之间。而对往来于福建、广州和东南亚之间的大商船来说,文昌的意义就不重要了。而澎湖列岛则构成了另一种情况,它们在经济上不重要,但却有供船只躲避风浪的作用,而且也可用来监控福建和台湾南部之间的航线,以及经过台湾海峡的交通。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军事上的保障,中国的许多港口就只能任凭海盗劫掠;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面积狭小,且在文献中往往极少提及的地方,比我们想象得要重要得多。最后,为了恰当地回答您的问题,应该发展出一套关于中国各港口、停泊港湾和岛屿的类型学,但是现在还没有。
南都:我很好奇,在古代如此有限的信息传递条件下,古代中国及东南亚各国,航海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们如何准确地获得各地的物质需求,并最终达成了贸易的往来?
普塔克:航海技术指的是什么?造船,航海知识,航海仪器?如果用古代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在许多领域,最晚从唐宋时期开始,就是亚洲领先的了。中国很早拥有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交通工具,船上有舱壁、舱房和巨大的储货空间,因此可以将大量的商品运输到目的地。我们今天也认为,许多信息都是从其他航海文化当中吸收来的。把中国的这些知识和葡萄牙文本提供的说明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很清楚地发现,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者们所拥有的知识是类似的。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时代里,关于价格和数量、市场和商人的信息是如何流转的,已经几乎无法确定了。我们一般只能说出一些笼统的结论:翻译、领港员和提供情报的人发挥了一定作用。而踏上旅途的人,也永远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拥有组织良好的船坞,员工规模很大,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在中国制造的船只数量极为可观,可能直到殖民时代早期,东亚和东南亚都居于领先地位。至于为什么最后从明代开始没有产生进一步的技术进步,这是另外一个长久争执不休的话题。
南都:我们知道指南针出现在宋朝,帮助后来的航海技术航行到更远,海上丝路有非常清晰的停泊地或者补给站吗?有无相关的研究成果?
普塔克:确实,指南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另外,我们也知道,航海者曾经跨越过遥远的距离,因为他们观察星辰和飞鸟,熟悉随季节而变化的风向和洋流,懂得正确地解读海水的不同颜色和许多其他自然现象。早在“海上丝绸之路”清晰显现之前,就有船从马来世界开往马达加斯加,横穿印度洋,而此时尚无罗盘。显然,这些勇敢的海员对他们生存空间的海洋非常熟悉。有时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疍家人等群体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张各种航线构成的网络,但是,如果没有像疍家人这样的海上群体和他们的航海知识,要把某些航线纳入这张网络,几乎是不可能的。换个说法就是:技术确实很重要,我们可以观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但技术并非成功的唯一前提。
关于补给站的问题,也就是后勤保障系统。船只和舰队规模越大,在海上的船越多,后勤保障就越重要。这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据文献记载,郑和率领着巨大的船队。比如,即便只有二十艘船,四千到五千船员,如果一下子到达马六甲,食物、衣服和供水是怎么解决的?当时的马六甲只是个小地方。这么一个小港口如何供应这么多人的衣食?简单地说,在记载大规模航海行动的时候,文献资料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船队的后勤保障系统是什么样子的。这非常遗憾。
海上丝绸之路仍有现实的启示
南都:有人认为,在1500年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是自东向西的,而随着欧洲人的海洋扩张,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普塔克:我在上面已经评述过,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段是在不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海和南海的部分,还有围绕着阿拉伯半岛的部分。也就是说,无论历史学家怎么描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自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都是一回事。他所必须做的,是保持公正客观,给出均衡中正的阐述。
我们当然可以把1500年前后的时代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但这么做也有风险,而且这也取决于观点。欧洲人带来了技术革新,甲板上安装了大炮,就有可能用较小的舰队控制一些海湾和港口,但却无法控制宽阔的航道和更广阔的海域。直到1600年以后,亚洲的情况才发生了明显变化:尼德兰人和英国人极具侵略性。他们洗劫外国船只,在陆地上进行破坏,而且往往对其他文化毫无理解。他们的兴趣是占领土地,控制货流和获取利润,试图强迫亚洲人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从另一个角度看,耶稣会士曾经尝试和中国以及印度受过教育的上层进行对话。也许在郑和时代,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尝试对话和交流的现象。而在主要受到新教思想影响的欧洲西北部人当中,就不存在类似的尝试。简而言之,除非想强调单纯的地理视角,否则,上述的这些思考可能就可以佐证1600年前后的时代更应该被认为是转折点的看法。
南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作用究竟有多大?
普塔克: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说,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非常重要。特别是许多文化元素的引入,在中国引发了若干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反之,通过自身商品和思想的走出去,中国也在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和声望。如果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中国就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当今的状态。当然,我们无法用数字对此进行衡量。不过,我的印象是,过去几百年以来,从整体上看,海上路线正在变得比陆上交流更重要。
南都:你如何评价海上丝绸之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作用?
普塔克:一般来说,港口和岛屿,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是积极事物。在今天,这有利于不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只有维持交流关系,我们才能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有些群体可以看作这方面积极的例子:比如郑和、葡萄牙人、耶稣会士,还有从印度去中国或者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佛教僧侣等。“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相互理解的轴线;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存在的许多积极面,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
南都:中国正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你认为有哪些意义是需要重新挖掘并加以研究的?
普塔克:我把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连在一起。中国一直强调,理解和交流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再补充一点,不同文化的所谓“价值体系”并不像人们声称的那样不同。我们要做的是把一切领域的积极事物聚到一起,强调共性,避免冲突,谨记只有在高度和谐之中,才能解决问题。
这让人联想到孔子的思想,还有其他宗教的一些教导。概括地说,对早先时代的“复兴”和“理想化”,也许能够积极地推动未来的塑造。虽然这显然是一种愿景,甚至也许只是一种乌托邦,但我们必须走这条路,并且怀着这样一种希望:人类的思想能够变得宽松自由,积极的观念将替代古老的敌对想象以及负面的偏见。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概念和行动的构想,不只有物质层面,还有深刻的心理学维度。这个构想既唤醒我们的期待,同时也是一种警醒。它展望未来,也许比其他“梦想”看得还要远。因为人若不能改变自己,那将发生什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和实践,我们必须持一种乐观的基本态度。这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意味着:源于自私思想的忧虑和恐惧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各种计划和愿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祝愿“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取得成功。
采写:南都记者 刘炜茗
(本次采访由南昌航空航天大学史敏岳先生翻译,特此感谢)
本系列访谈,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南方都市报共同策划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