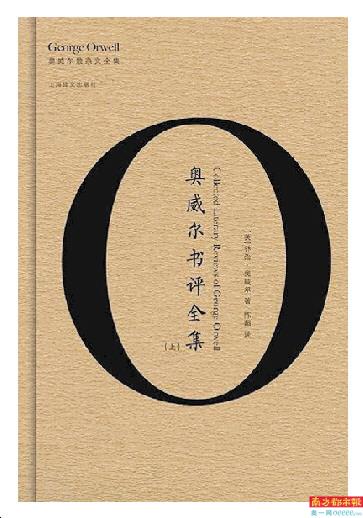
《奥威尔书评全集》,(英)乔治·奥威尔著,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月版,198.00元。
□乔纳森
如果说在普通人眼中,最具英国特色的东西是板球、福尔摩斯和红色双层巴士,那么在写作的人眼中,至少是在我眼中,最能代表英国的,是它的书评。不必远溯赫兹里特、麦考莱,只看二十世纪,英国的书评家就层出不穷了,学者教授擅长评骘高下自不待言,即令是小说家、诗人,也照样写得一手好书评。小说家如伍尔夫、阿尔多斯·赫胥黎、伊夫林·沃,诗人如艾略特、奥登,可不都是一流书评家?
英国书评之佳处,在能以常识为底蕴,做简洁精炼、一针见血之评价。这里的“常识”,不是指凡夫凡妇的日常知识,而是指知识人以平素见多识广的博杂学识夯筑的,融知、情、理为一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当然得之匪易,亦不寻常,之所以仍标一“常”字,是因为它从来不远于常理常情,无论多么深厚或复杂,总是从人的日常处境中生发而出的,因之凡有所言,皆能结实练达。
上述佳处,在乔治·奥威尔的书评中体现得相当充分。假如我们要给奥威尔的作品打分,他那些带有政治指涉的小说恐怕顶多只能打七八十分,而他的书评、专栏却很可以打九十分以上。新近出版的三卷本《奥威尔书评全集》,让我们有机会饱览“高分”书评——不单单是了解奥威尔个人的文字成就,同时亦将领略英国书评的高妙境界。
奥威尔的学术背景,自不足与学者教授相抗,但他阅历丰富、阅读广泛,加以理性强健,而在审美方面,则富于艺术家的直觉,敏锐且能兼收并蓄。奥威尔具备成为优秀书评家的条件,固然难得,不过更重要的是,写书评,像宰牛杀猪一样,光有上好的资质还不够,技艺非得在千万次的具体实践中反复磨砺过才行。奥威尔是书评事业的伟大实践者,《奥威尔书评全集》汉译本将近1600页,数量之巨,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奥威尔写书评之勤,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且以他写作最多的1944年为例:当年他一共写了58篇书评,涉及的书超过83种。从频率来说,他平均不到一周就会写一篇书评,四五天就会读一本新书。我们不要忘了,他那年还写了小说《动物庄园》。
奥威尔的书评中涉及时事政治者不少,而以他在缅甸殖民地、西班牙内战中的经验和体会为基底,这些书评往往眼光犀利独到。当然,写得最出色的,究竟还是文艺方面的评论。奥威尔多次评价亨利·米勒,初而赞赏但有所保留,继而悟今是而昨非,将评价的调门调得更高,甚至以亨利·米勒为重要基点,写下他最有影响的名文之一《在鲸腹中》,再后来,他渐对亨利·米勒的作品失望,对其做了重新审视。借由这多篇书评,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文艺观念的嬗递之迹。不过,最关键的是,当《北回归线》一问世,奥威尔便马上洞察到它的成就和重要性,没有被其题材的表面争议性所蒙蔽,而是着眼于其艺术上的独创。这是一位称职的书评家最值得夸耀之处:他能在成千上万纷繁芜杂的书籍中迅速锁定那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几种。
对同辈人使用的批评语汇,奥威尔曾屡致不满,比如他认为书评界的一大困境是“对于真实价值相距万里的书籍,无论是褒扬或贬斥,用的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词语”。有些书形同垃圾,可书评家也不能不打起精神,认真对待,而这则“意味着用上那些你准备用于评述司汤达或莎士比亚的作品的词汇”。奥威尔精辟地说:“这就像用一台给鲸鱼称重的秤去给一只虱子称重。”其实,奥威尔评论过的书,许多也不过只有“虱子”的重量而已,然而这也往往考验书评家的品质:有操守的书评家总是会变着法儿地把自己的书评写得漂亮,而不管被评的那本书有多烂,这也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去读奥威尔评论的很多书却不介意欣赏他的书评的理由之一。
《奥威尔书评全集》三卷,篇幅如此之巨,我们对译者不能不怀有感激、钦佩之情。自然,这里面难免有些失误的地方,好在多数影响不大,而译者文笔畅达,也常使人忘却那些差错。令我稍感不适的,是书中人名、书名不合惯例者甚多,这里姑举几例。全集第1516页文章《乔治·基辛》,按,应作《乔治·吉辛》。这是奥威尔很有名的文章,有不同译者译过。文中提及一本书,叫《亨利·莱克罗夫的私人文件》(第1517页),按,这是照英文字面硬翻的,此书一般译为《四季随笔》,有多个汉译本。再如,《皮尔斯·普劳曼》(第61页),原文Piers Plowman,这是有名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有汉译本,Plowman,犁人、耕者也。又如,奥威尔评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书《创伤与鞠躬》(第605页),这本书许多文学批评论著都会提及,通译《伤与弓》,Bow是多义字,此处不是“鞠躬”,而应是“弓”。为什么是“弓”呢?译者如果看过威尔逊那本书就会明白,书中有一篇文章,叫《菲罗克忒忒斯:伤与弓》(Philoctetes:The Wound and the Bow),书名就是打这儿来的。菲罗克忒忒斯是《伊利亚特》里的神话英雄,曾被蛇咬伤,而他是希腊第一的神箭手,弓箭为其武器。我们不能指望译者对所译的内容了解到作者那种熟悉程度,所以偶有差池,殊不足为怪,只是像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种水仙的黑人》(第1108页),通译《“水仙号”的黑水手》,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物质的心》(第1538页),通译《问题的核心》,这些算是近现代的文学名著,而译者居然不知,就未免令人讶异了。不过,说到底,对《奥威尔书评全集》是怎么推崇揄扬都不过分的,能在汉语里读到这部庞大译作,实乃吾辈之幸。

